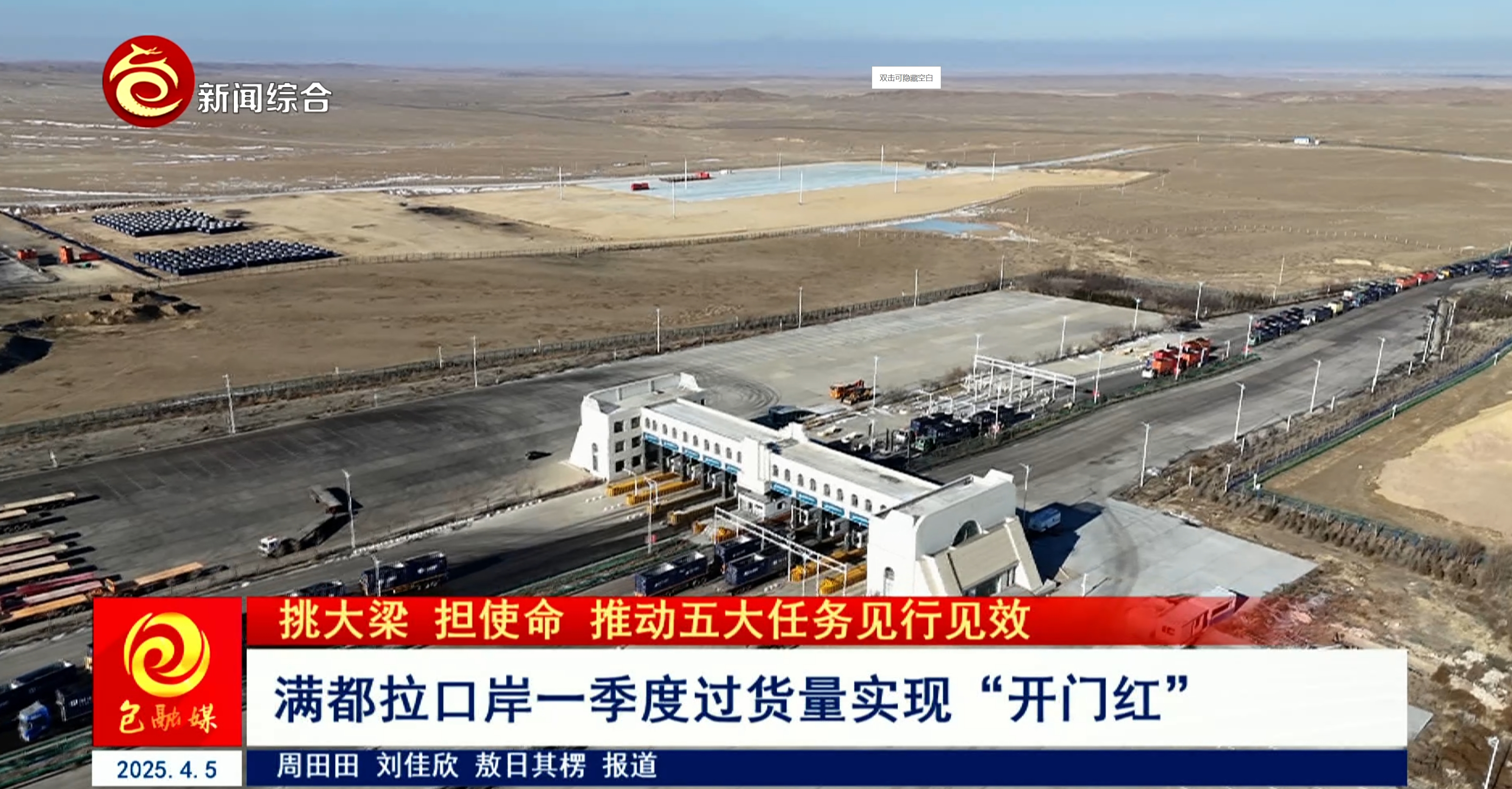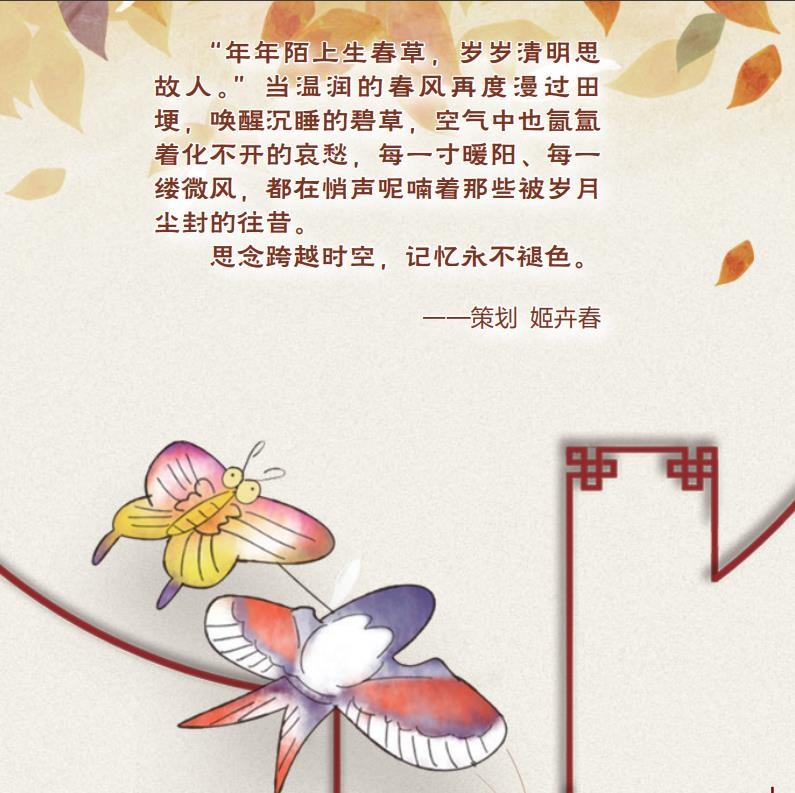
父亲和他的土地
□牛银万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不知道粮食中含有多少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只知道它关乎人的生存,只知道粮食来之不易。
每年麦收后,父亲都要一个人反复在地里捡遗失的麦穗。若碰到老鼠洞,他还要用铁锹挖开,“抢”回被老鼠盗进洞里的麦粒。麦子碾压后,打麦场上会压进很多麦粒,他总要蹲下一颗一颗地去抠。有实在抠不出来的,再把家里的鸡赶来。鸡啄的时候,父亲就坐在麦秸堆旁,手里挥动一根长长的树枝赶鸟。打下的麦秸,少部分用于春天和泥抹房,其余的都用来炉灶烧火。烧火前,父亲会摊开麦秸,让鸡再啄一遍。
秋天掰玉米,父亲一遍遍翻开码放在一起的秸秆认真检查,看还有没有遗漏的玉米棒,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他也不放过。掰下的玉米棒拉回家,风干得差不多时,父亲就和我们坐在院中搓籽。父亲搓玉米特别快,我们搓一个,他就能搓两个,而且搓得一粒不剩。
父亲从来不剩饭,每次都把碗扒拉得干干净净。对不小心掉在炕上或桌子上的米粒,他就用粗壮而结满厚茧的手指,慢慢捻起来,一粒一粒送进嘴里。为此,我们很不理解,开玩笑数落他:“咱们家再缺粮也不缺这一点儿,让院里的鸡和狗也吃上点吧。”他却认真地说:“浪费了可惜,遭了年景你们就知道了。你们不记得小时候了?”
因产量低,后来,父亲就慢慢不种小麦糜谷了,而种上了玉米。于是,吃米面只能去买。可总觉得买回的米没有香气,焖出的饭色泽灰暗,吃起来很粗糙;白面也不如自己种的筋道。
于是,父亲腾出一块地,又种起麦子和糜谷来。
每次回去,在吃米面时,他不停地自夸:自己种的就是好吃。等我们走的时候,也总要大袋小袋,执意给我们带上。
父亲生病时,最爱吃面条、喝小米粥。母亲擀的面条又细又长,浇上腌猪肉和土豆块熬的臊子,味道绝佳,父亲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喝小米粥时,他就着烂腌菜能喝三四碗。然后,心情舒畅地躺在炕上,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父亲早饭爱吃酸粥。他让母亲一年四季在锅头的罐子里,浆着自产的小米。吃时就着烂腌菜或撒上胡麻盐,一口气能吃两三碗。吃完酸粥,父亲再把锅巴铲出来,在碗里泡着酸米汤吃,不浪费一点儿。
夏天,父亲最爱吃焖酸米饭,老家叫酸捞饭。午睡起来,他常常装一瓶酸米汤,下地慢慢喝,酸米汤既解渴又解暑。
父亲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在院中靠墙的地方,挖了几个地窖,铺上麦壳和麦秸,把多余的小麦储进去。每隔一段时间取出来晾晒两天,以防发霉。实在储不下时,他就把小麦磨成面粉去卖。老家的小麦品质好,磨下的面又白又筋道,远近闻名,买的人很多。
父亲管理庄稼特别用心,他把田间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别人锄一遍他锄二遍,别人锄二遍他锄三遍。为了不错过浇地的日子,他披星戴月,半夜就起来,蹲在渠边等水。因买不起化肥,闲下的时候,他就挎着箩筐到野外拾粪。
为了增加产量,父亲在麦田中套种上黄豆。小麦收割后,灌一次透水,黄豆苗马上就一片葱绿。为了不浪费土地,父亲又在田垄上点上蚕豆。黄豆喂羊、生豆芽,蚕豆数量少,逢年过节给我们炒着吃。
困难年代,村里种的糜谷和小麦,大部分交了公粮,返销粮都是清一色的玉米面,早晨玉米糊,中午玉米窝头,晚上玉米拿糕。那时我们还小,吃腻了难以下咽,父亲却大口大口总是吃得很来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有了自主权,父亲每年都要种几亩小麦。即使这样,过年时,家里除了篜足够的馒头,还要篜一大盆玉米面发糕。父亲这样做,一是换换口味,二是让我们不要忘本。
如遇灾年,父亲时不时站在粮仓前,默默计算着粮还能吃多久。如粮少,他就反复安顿母亲,尽量把饭做得稀一些,吃饱就行。当听到有的地方受灾,庄稼被淹粮食减产时,他忧心忡忡,不停地叹气。
一次,他在电视里看到国家倡导“光盘行动”,猛地坐起来,激动地说:“早就该这样了,大吃大喝不心疼,不知道浪费掉多少了!”冬天,每当大雪纷飞时,他坐在窗前,一边抽旱烟,一边望着窗外,高兴得合不拢嘴:“瑞雪兆丰年,下哇,好好下,明年又是丰收年!”
他经常劝我们多吃粮食少吃肉。当得知我们晚饭喝开玉米糊时,他特别高兴,一下磨了一大袋玉米面,让我们带回去喝。
每逢祭日上坟时,父亲带得最多的就是馒头。他把又白又大的馒头摆在墓碑前,烧完纸,掰成小块,认真地泼撒在坟上。
父亲生前最牵挂的,就是他那片心爱的土地。一再安顿:他走后地不要包出去,钱少花不咋,没饭吃就麻烦了。
父亲一生勤劳,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他深知土地的意义,深知粮食的珍贵。他用自己的行动,让我深刻理解了“民以食为天”这句谚语的真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对土地的敬畏,对生活的执着,以及对家人的深深牵挂。

姥姥的爱与温暖
□越慧贞
姥姥去世多年了,但我还常常在梦里见到她。醒来也不觉得悲伤,反而有一种见到面后的满足感。我常慨叹,姥姥就是这样的好老人,活着的时候,你能享受到她的亲情,去了的时候你也觉得安心。
我认识的女人中,能称得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莫过于我的姥姥。姥姥除了在我们姐妹力邀之下,来我家吃顿饭,或是到自家地里摘点豆角黄瓜,其他时候绝少出门。村里唱戏和赶交流,想叫她出去转转那是不可能的,她仅仅是站在院里听听喇叭里放出的戏声。正月里闹红火的来了,我说:“姥姥,我扶你出去看看。”“他们要走门前咱们就看看,要不走就算了。”姥姥说。
姥姥虽然不出门,但我们将在外面经见的事说与她听时,她总能说出些道理,让我们知道对与错。无怪乎三舅常对我说:“你姥姥是不识字,那要是识字,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姥姥不识几个字,只会看日历,认得二十四节气。
我常看见村里的老人们聚集在阴凉地,东家长西家短,衣服邋里邋遢,姥姥从不那样。姥姥的衣服总是朴素干净,有时我们给买点衣服,上面有花的她总不大穿,若有绣花,她会仔细地拆掉再穿。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地里帮忙,无意中起身瞭望,远处田埂上,姥姥缓缓而行。田埂上草长得高而茂盛,姥姥白净的脸庞,玉青的中式罩衫,就是一幅素净淡雅的画面,让我不禁叹道:“真好看啊!”
冬天家里杀猪或宰羊后,总要弄些杂碎吃喝。姥姥嫌媳妇们没耐心,总是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淘洗,杂碎熬好了她却一口不吃。夏天舅舅们常弄回些鱼来,也是姥姥细细地收拾了做好大家吃,姥姥却只吃一碗粥。姥姥最爱吃的饭有两样,面和粥。有一次三舅来坐了一会儿,临走姥姥问:“不在这吃饭?”三舅说:“不了,家里吃饺子了。”姥姥送出门:“那就不留你吃饭了。”三舅问:“吃甚呀?要吃面我就在这儿吃呀。”我在屋里听到差点笑坏,饺子都赶不上我姥姥一顿面香?我姥姥孙子外孙十来个,我们成天不想吃家里的饭,就去姥姥家吃,就是稀粥,姥姥也能熬出不一样的香来。
每年天冷时,姥姥就会做些她和姥爷的针线活。妈妈是助手,我是观众,看着一件件中式的袄裤从姥姥手中诞生。我有时惋惜地说:“以后我们不会这些,太可惜了,手艺要失传了。”姥姥总是笑笑说:“你们这会儿幸福的,哪用做这些,买着穿就行了。”但我常被那极其简便的缝制方法所吸引,被那极其合理的成衣方式所折服。尤其是制作纽扣,先把细布条缝缀成圆滚滚的布线,再弯弯绕绕地穿成一个个“桃疙瘩”,一个个布纽就成型了。
姥姥不仅针线活儿好,剪纸也很拿手,周围的人家过年或娶媳妇,都会拜托姥姥剪些花样作装饰。手巧之人必然心灵。我读初三那年常住在姥姥家,电视上正播放《上海滩》。晚上姥姥看电视,我在隔壁小屋里写作业,晚上睡觉时,就问姥姥当天演了什么情节。姥姥会详详细细地给我复述一遍。有一集里,冯程程换了个新发型,头发怎么向后挽起,怎么盘卷成型,姥姥讲给我听,令我充满想象。多年后重看《上海滩》,看到那一集,一见冯程程的发型,和我想象的竟一模一样,令我更加佩服姥姥的聪颖。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姥姥的审美趣味很高级,穿的用的东西都充满了美感,就连我们姊妹几个帮姥爷下柿子时,每人手里拿着的一个红柳篮子,也是别人家没有的,不大不小,精致漂亮。
现在和弟弟妹妹们聚在一起,也总要说起姥姥,不止一个人说过“姥姥最亲我了”或“娘娘最亲我了”。有时也会引发小小的争论:“要不是了,姥姥还是最亲我。”大家便抢着回忆往事,来证明姥姥最亲的是他。那些回忆里,藏着姥姥无尽的爱与温暖,藏着她对每一个孩子的偏爱与关怀,更藏着我们深深的思念。

方言“指挥家”
□刘英瑛
我大概从出生起,就住在姥姥姥爷家。17年前,姥姥去世了,留下姥爷一个人。
姥爷身材偏胖,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总是操着河北方言,在家里指挥这,指挥那,眼睛一瞪,大家都得听他的。
姥爷退休前在厂里搞工会工作,“说话”是他最擅长的,不是因为他搞了工会工作才擅长“说话”,是因为他擅长“说话”,才有了这份工作。
姥爷来包头投奔亲戚的时候已近30岁,起初在厂里干装卸工。“太累了,我年龄大了,根本干不过后生们。”一次无意的对话,他给我讲起了他早年的经历,“我是党员,以前在村里当过村支书,靠这些经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办公室,干工会工作。”
工作期间,姥爷帮助厂里的工人维过权,厂子倒闭后,又给大家张罗退休金……忙前忙后,全凭他这一张嘴。当然,用来教育我也是一套一套的。他最喜欢在“指挥”我学习的时候,摆出我舅舅的例子——舅舅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十分稀缺,学习优秀自然没的说,据说生病20天后,去学校考试仍是第一名。舅舅入伍后,政府给姥爷颁发了“光荣之家”的牌子,牌子现在还在姥爷家端端正正光荣地摆着。
记忆中,姥爷总是带我去体验我没干过的事:他带我去吃烧麦,8岁的我一顿就能吃8个;看到报纸上说银河广场有水幕电影,他大白天就带我去看,当然是没看到;听说哪里赶交流,他就带我去凑热闹,结果误入了一个跳脱衣舞的演出大棚,他慌慌张张赶紧把我带了出来;我没坐过火车,为了让我体验一下,姥爷带我从包头东站坐火车去了一趟包头站……
姥爷管我特别严格,指挥着我的方方面面。小时候的家长会都是姥爷去开的,我学习成绩好了,他会表扬我,学习成绩下降,他又会搬出舅舅教育我。直到上了大学后,姥爷还会规定我晚上回家的时间。当然,在我的吃喝上,姥爷也功不可没,从小胖到大的我,就说明了一切。结婚时,为了穿上美美的婚纱,我花了大价钱减肥,结果姥爷见了我,泪眼婆娑:“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
后来毕业了,结婚了,生娃了,去姥爷家的次数也少了。每每路过姥爷家,总是看见他戴着凉帽在楼下“指挥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和他们打扑克。那个时候的他把烟酒戒了,身体还算硬朗。
疫情期间,姥爷不幸得了肺炎,发展成白肺,经过医院的全力救治,姥爷虽逃过一劫,身体却大不如从前。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还是喜欢“指挥”儿女们每天早晨给他买烧麦、每周六带他下馆子。到今年春节,姥爷已经离不开制氧机了,那次生病带给他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后来,制氧机加到了2个、3个……
我的名字是姥爷起的,他也曾给我算命,说我定穿紫袍——“古代当官的才穿紫袍”,他总是这样解释。他也总是问我考编考得怎么样了,可我不才,马上超龄仍然没有上岸。今年考试一结束,我匆匆回到姥爷家,看到骨瘦如柴的他眼睛闭着。我轻轻唤他,他才眼皮微抬,看着我点了点头。我试着给他喂水,他勉强喝了一点儿。次日早晨,姥爷闭上了眼睛,他大抵是在等我,想再问我一次“考得怎么样”吧。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