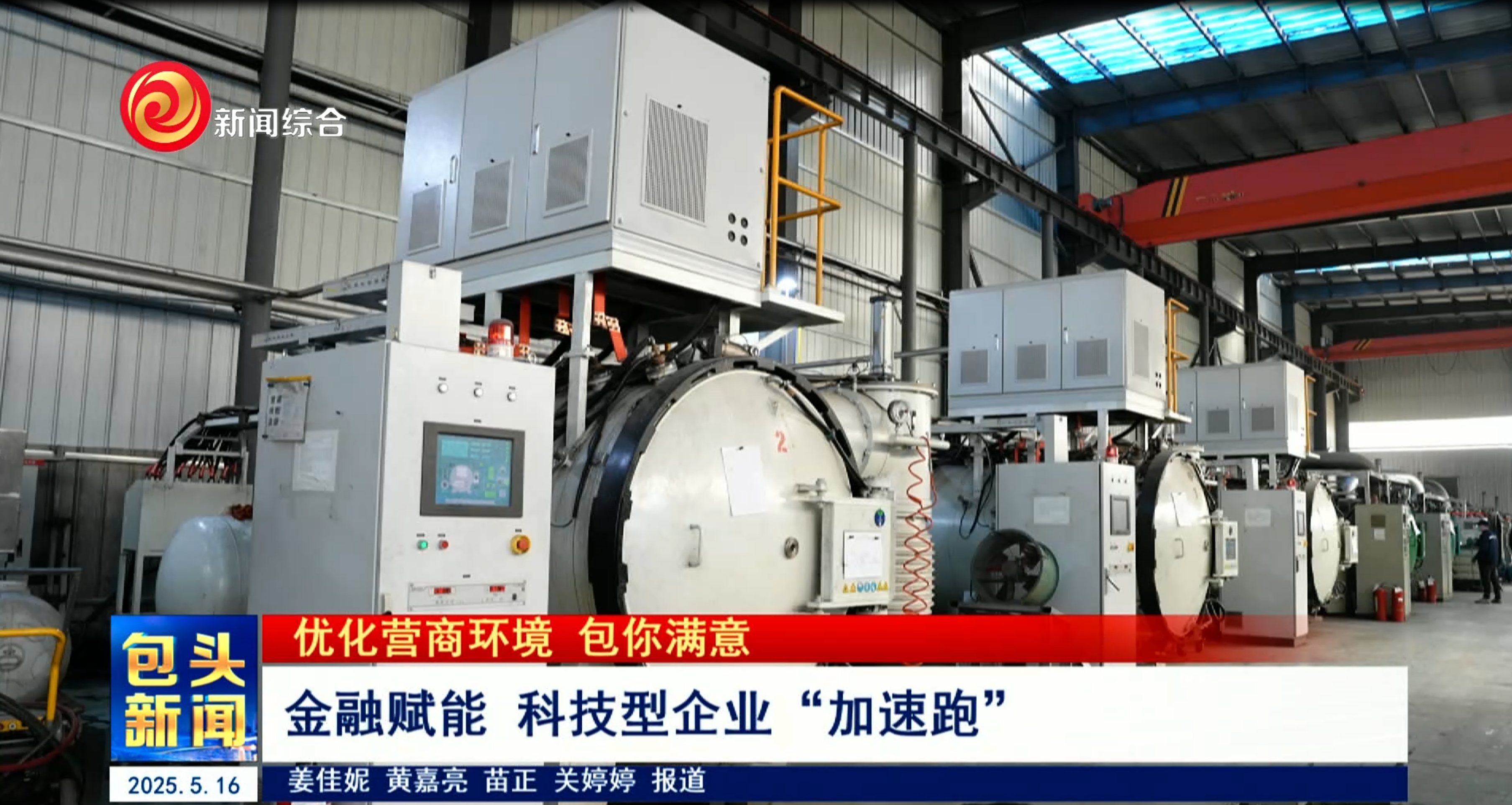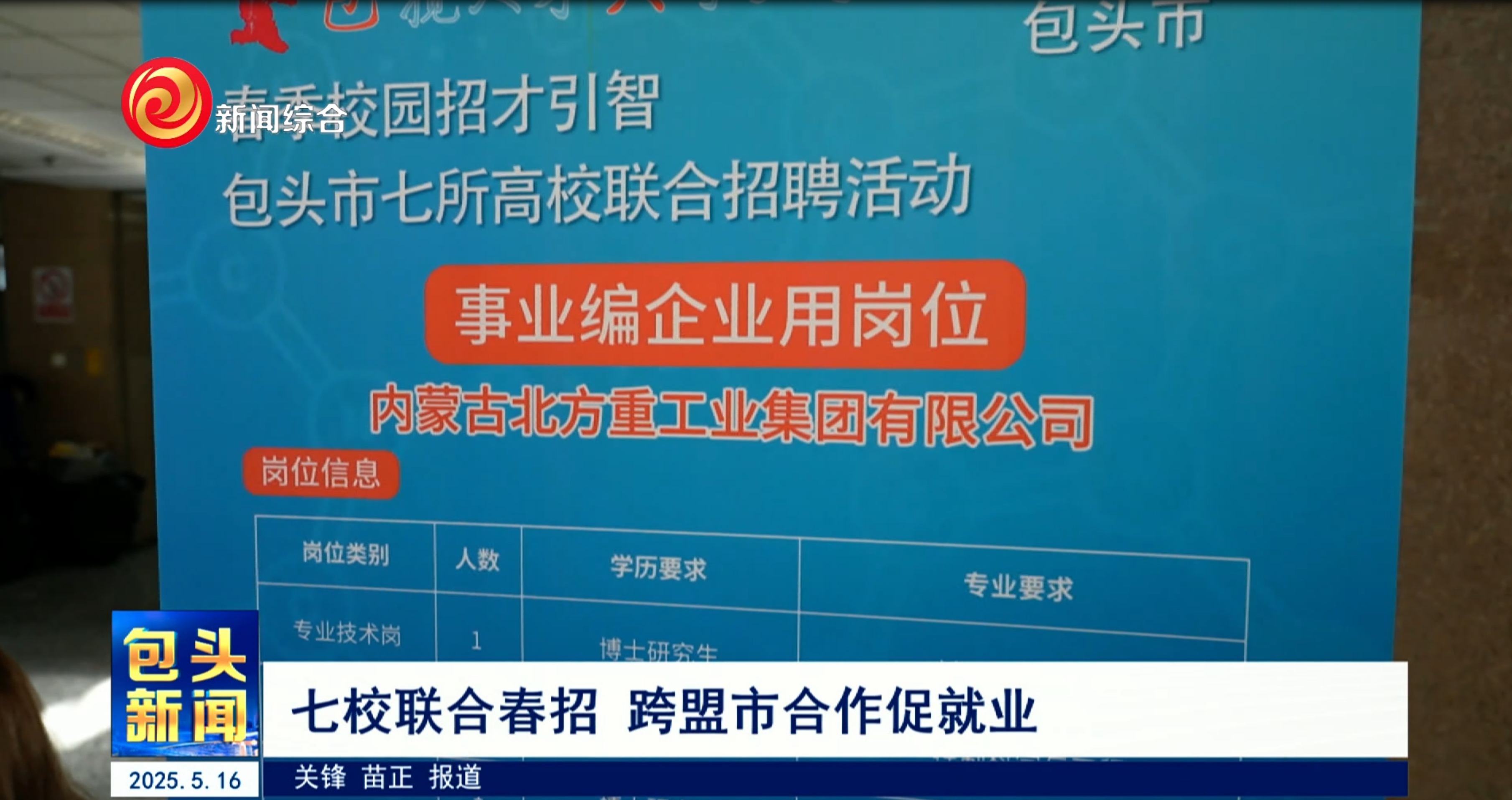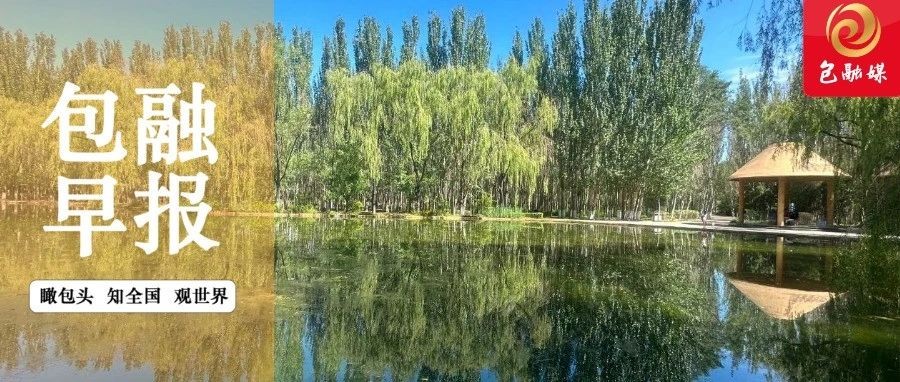赵永峰 摄
开栏的话
本土文学,宛如这片土地上最悠扬、最动人的歌谣,它承载着我们共同的珍贵记忆,凝聚着我们深沉的情感,忠实记录着时代的沧桑巨变与人民的烟火生活。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高的敬意与满腔热忱,推出“经典回响”这一全新专栏,精心为读者们呈现本土名作家的经典文章,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学瑰宝,再次于时光的舞台上绽放夺目光彩。
这些经典之作,恰似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包头的精神风貌与灵魂底色;又似一汩汩清冽的甘泉,静静流淌,滋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让我们在喧嚣纷扰的尘世中,得以寻得一方宁静的绿洲,找到心灵的慰藉与归宿。
——姬卉春

□许淇
即使冰冻的泥土也会被岁月焐热,因为青春犹如矿藏的潜能令春天永驻。
我虽然不是昆都仑河两岸的拓荒者,但我是一名青年建设者。建设者,光荣的称号,让人联想到冰天雪地里保尔的形象和他那使整整一代人倒背如流的语录。那时候,包头团市委办的一张报纸就叫《青年建设者》。我负责编副刊《摇篮》,建设者的诗歌就在草原马背上的“摇篮”里诞生。
我曾经写过《钢铁大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写到一个上夜班的老工人在钢铁大街上遇到一只狼。我曾经写过《人民日报》的“名城赋”专栏,歌咏塞北这座新兴的城市。
我曾经参加包钢高炉出铁的庆典。我离主席台很近很近,看见周恩来总理轻轻地有节奏地鼓掌。
我欣赏了马连良先生的艺术,不是在京都吉祥戏院或是津门沪上著名的大剧院,而是在包头的昆都仑恰特,如今已显得陈旧了,而当年它却是何等辉煌!
黄河岸边的几个村落,我吃过蒙古族乡亲们的酸捞饭。我居然在北方学会插秧和栽种水稻。修渠我唱自编的夯歌,拔麦子勒出个血手掌。在接近托克托县的黄河边,有一块肥沃的河滩地,归一名“知青”播种。他独住在河边小屋,晚间我躺在他的土炕上,听他对着灯呱呱坠吹“枚”(笛),然后枕着寂寞的潮声入梦,天还未亮,密集的湖鸥锐利的鸣唱唤醒了我……曾经多少萍水相逢的人物和风景呵!
北面的大青山和乌拉山我曾经攀登,大桦背的桦林、九峰山的清涧,像一册经常耽读的无名诗人的诗集。困难时期,为了逃避饥饿,市里有意组织干部到后山“秋收就食”,我们就以写“公社史”的名义,心安理得地坐到莜面荞麦丰收的老乡们的炕桌上。在高山深处的耳沁尧,“跌死虼蛉碰死蛇”,当第一辆客车开到山村,我也不禁和那一辈子没出过山的老娘娘一样,噙着泪,抚摩了一遍又一遍……
呵,这一片热土的角角落落都留下我的踪迹。
最初我是个年轻的单身汉,不免有“江南游子”客居他乡的相思,双老健在,我每年必南归省亲。返回包头,当我扛着行李在车站下车,那漫天的风沙和熟悉的方言,又唤起我本土方为“家”的强烈感觉。正如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所说:“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作客在上海的亭子间和阁楼,我是什么也做不成,而这里却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待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之后,倦游归来,便见月台上妻和小儿女迎接着,到家了!到家了!土居狭隘生活清寒,也有亲切的笑语,人间的温馨,也有一炉好火、一杯薄酒,这就够了!足够足够了!
每一道历史的褶纹都刻印在我的脸上,每一阵政治风云都波及我的朝夕,在这片热土上,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故事,或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真不知从何说起,或可滔滔不绝或竟是无话可说。
如今不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反而雏鹰高翔了。有的闯荡到国外,在美国、日本,都会遇到包头人,照样别墅汽车,拿到绿卡签证;有的到沿海地区当白领“打工仔”,不甘做边远地区的“乡巴佬”,潇潇洒洒走一回。我老了,走不动了,经常写信婉谢朋友的邀请,年复一年地蛰居蜗角,视旅行若畏途,远方的地平线不再燃烧我信天翁式的渴望。双老皆作古,原来的家乡变得不可辨认,真正地陌生化了,于是我竟然说:咱们包头人如何如何!我已和这方热土融为一体了。
看来我的结局将不可避免……跨世纪的未来的人们呵,届时请为我送行;一粒种子落归大地之时,我的灵魂才扬帆起程,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许淇(1937—2016),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包头市文联主席、《鹿鸣》主编、内蒙古文史馆馆员、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水孩儿
我在普救寺遇见了一只猫。
那是一只黄斑虎猫,很瘦,右腿上有伤,我踏入普救寺的那一刻它就认出了我。
坐落于永济市的普救寺,不仅是《西厢记》故事的发源地,更是无数情侣心驰神往的牵手打卡圣地。踏入普救寺,沿着蜿蜒而上的阶梯前行,便能瞧见密密麻麻的同心锁系在一旁。那些锁,锁住的是恋人们对爱情的美好祈愿,可不知为何,在某些瞬间,它们又像是无形的枷锁,在讲述着没有后来的故事。
正欲拾级而上,冷不丁,侧房屋檐上一只猫忽然窜到我跟前。它对着我“喵喵”叫起来,那叫声,仿佛带着某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好似它已然认出了前世的我。我每踏上一个台阶,它的声音便愈发急切,围绕着我不停地打转,看得出它想跳下屋檐靠近我,却又带着几分畏惧,犹豫不决。我见状,努力地伸长手臂,试图将它抱入怀中,然而指尖与它始终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终究未能如愿。
望着这只猫,我不禁心生怜悯。它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过往?在前世,它又与我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姻缘呢?
想起前两年,我在内蒙古大学进修,与青春洋溢的大学生们一同生活在校园里。每至毕业季,校园的角落里总会悄然出现许多流浪猫的身影。这些猫咪,大多是毕业后即将各奔东西的男孩女孩们无奈留下的。秋天的时候,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草地上,那些流浪猫便在树下寻觅着食物。它们或独自徘徊,或三两结伴,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努力生存。
可是,严冬一到,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纷飞的大雪席卷而来,不少流浪猫没能抵挡住这严寒,在冰天雪地中被无情地冻死。每当回想起那些被雪掩埋的小小身影,我的心里总是涌起一阵酸涩。不过,也有一些顽强的生命存活了下来。校园里善良的宿管阿姨们,于心不忍,便将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收留在寝室门口。在阿姨们悉心的照料下,这些猫咪们有幸存活了下来。
来年春天,我惊喜地发现,又有一窝一窝的小猫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它们在草地上嬉戏,在花丛间穿梭,有时候也会偷偷被女生抱回寝室收养起来。但是秋天,它们又成为被遗落的青春碎片,在校园的角落里独自承受着生活的风风雨雨。它们的存在,是对大学生们青春岁月的一种别样见证,见证着他们的成长、离别与无奈。
不管是普救寺的这只猫,还是内蒙古大学那些流浪猫,它们都是生命长河中的小小存在,在各自的环境里经历着生存的考验。普救寺的猫,在这承载着浪漫爱情传说的古寺中,或许也见证了无数情侣的悲欢离合。更或许,它本就是前世与我有过一段情感纠葛的某个人呢?
站在普救寺的阶梯上,我再次望向那只猫。它依然在屋檐上徘徊,那叫声像是在呼唤走失已久的恋人。
我看着它,忽然想起衣袋里有一袋奶酪,便掏出来放在掌心,尽力向前递去。它的双爪踩在屋檐的瓦片上,努力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食起来。它的舌头粗糙,刮得我手心发痒。
同行的友人笑问:“它认得你吗?”
“不认得吧!”我答:“也许它只是饿了。”
友人笑笑,说:“可是它好像只认你。”
我不置可否。想起那些同心锁,想起校园里的猫,想起生命里来了又走的人。爱情大约也是如此吧,以为是独一无二的相遇,其实不过是又一次重复的乞讨与施舍。
奶酪吃完了,那猫仍不肯走,在我头顶的屋檐上徘徊。我仰头看它,它低头看我,彼此都有些不甘心。我想抱它下来,却又够不着;它想再讨些水喝,却又下不来。僵持了一会儿,我终于狠下心来转身,向着普救寺的塔顶登去。
或许,它只是偶然间对我产生了好奇,而我却赋予了它如此多的遐想。但这又何妨呢?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相遇与联想,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独特馈赠。
阳光下的普救寺依旧静静地矗立着,迎来送往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我离开普救寺时,那只猫又出现了。它躲在门口的石墩后面,远远地望着我。我向它挥挥手,它叫了两声,便转身跳下石墩,消失在寺庙中。我想,它大约是怨我狠心离开了,又大约是在等待下一个手里有奶酪的游人吧。
同心锁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又仿佛只是被风吹动了而已。

□周静
五一小长假,帮母亲整理衣柜时,我发现一件眼熟的粉色坎肩。
“这不是我那件十几年前的外套吗?”我问母亲。母亲慢悠悠地说:“我把它改成坎肩了。”母亲已到了古稀之年,对缝缝补补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
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只读过两年书的她很能吃苦,从小就帮家里干活,洗衣做饭、纳底做鞋、锄地割草,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心灵手巧的她年轻时跟村里的老师傅学过裁缝。二十一岁时成家后,每天与父亲早出晚归,耕田种地。
等有了我和弟弟,母亲白天就更忙了,只有晚上她才能闲下来做针线活。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总是低着头,隔一小会儿,会把带着长长丝线的针在头发上擦一擦,再去缝制衣服,如此反复。到了冬天,我们姐弟俩趴在铺着油布的炕上写作业,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缝补衣服。冬天的夜漫长又寂静,写完作业的我们,早早就钻进暖和的被窝里。母亲却仍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那一下接一下的“嚯嚯”声,在寒冷的夜晚显得温暖又甜蜜。
几年后,生活稍稍好了一些,父亲托人从外地买了一台前进牌缝纫机。母亲高兴极了,满眼含笑,不停地打量着这台渴望已久的缝纫机,用她那粗糙的手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如同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母亲做针线活再也不用发愁了,改衣服、缝新衣的效率高了,夜里缝纫机“哒哒”声持续时间也更长了。
小孩子总是长得特别快,头一年穿着还算合身的衣服,到了第二年就短了一大截。母亲的手艺有了大用场,她一会儿用尺子量一量,一会儿用剪子剪一剪,一会儿又坐在缝纫机前,左手捏住布料,右手旋转机轮,双脚匀速踩动踏板,布料沿着针头缓缓前行。工夫不大,又小又短的衣服就“变”大了。我们姐弟俩穿着母亲缝制的“新衣服”在村里四处疯跑,如果被爱美的孩子和村里的大婶们看到,接下来我家肯定会热闹好几天。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我做的花格子书包。布料是母亲从剩下的花布头上剪下来的,方方正正,花花绿绿。然后用缝纫机一块连着一块拼接缝合而成,既结实又好看,正好装下我的课本和铅笔盒。我斜挎着花格子书包去上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连路边的花儿草儿似乎也在跟着我一起跳跃。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便更加得意,仿佛那书包里装的不是书,而是某种荣耀。那是母亲所期盼的一种“荣耀”。
后来我当了老师。学校举办30周年校庆活动,要定做一批桌套。校长得知母亲学过裁缝,便把这差事交给了母亲。那段日子,家里堆满了蓝色的布料,空气中飘着新鲜的棉布气味。母亲从早忙到晚,常常顾不上吃饭。夜深了,缝纫机仍不时传来有节奏的声响,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伴我进入梦乡。校庆那天,全校课桌都“穿上”了母亲做的蓝桌套,齐齐整整,成为教室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当我走进教室,望着这些格外鲜亮的蓝桌套,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自豪。
再到后来,我们都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就亲自给孙子、外孙做衣服,在她看来,买的衣服远远不如她自己缝的舒适、放心。
岁月流逝,母亲老了,眼睛也花了。可她放不下那台缝纫机,仍旧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至今家里还有母亲给我们全家缝的棉拖鞋和鞋垫。母亲还会突发奇想,将旧外套改成马夹、半袖改成背心,甚至还会做八角帽……每次都会高兴地给我分享她的“杰作”。
近些年,母亲身体大不如前,终于不得不与缝纫机告别。卖掉它的那天,母亲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久久地望着那个空出来的角落。在母亲眼中,那绝非一块空荡荡的地板,而是四十多年来在缝纫机前度过的日日夜夜——那些为家人缝制的衣物、那些为生计赶工的辛苦、那些将爱意缝进一针一线的时光……

□漠津
父母的爱子之情中有喜爱小猫小狗般轻佻的成分,爱其娇弱温顺。当孩子渐生出意志和自尊,这部分喜爱便会急剧消退。这是女儿毛豆三岁半时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
起初,我是在爱人春雪的身上发现了这一端倪。
曾经春雪是一个为满足毛豆需求不顾后果的母亲。我们推着婴儿车穿过一个繁忙路口的非机动车道时,毛豆大哭,春雪不顾来往密集车流,当即将一米多长的婴儿车横置车道正中,屈身为毛豆更换纸尿裤,右转的电动车纷纷急刹、拥堵一团,甚至将占用辅道右转的机动车都挤到了主道上。一时漫骂鸣笛声大作,春雪如梦初醒,才将婴儿车推到一步之遥的人行道上继续伺候毛豆,压根没意识到自己方才的举动多么危险荒唐。毛豆未满周岁时睡觉极轻,我们便不敢在午夜孩子熟睡前如厕,深恐冲厕声惊扰毛豆再生事端。
好像一条脐带仍然连接着母女,孩子的痛苦会成倍地放大于春雪之身,将她变作了一具丧失理性和自主意志的傀儡。她将自己作为母亲的严苛标准套用到我和毛豆奶奶身上,许多难解的积怨因此萌生。彼时我一大心愿就是,春雪能脱离毛豆的操控,稍稍宽待自己和我们。这个愿望在毛豆两岁半左右实现了。一日,春雪刷着抖音再三挣脱孩子不得,忽然厉声吼道:“你就不能自己玩一会儿!”
方才还张牙舞爪的毛豆被这声怒喝定在了原地,活像深夜被突来强光吓破胆的猫头鹰,缩着脖子瞪着春雪,乍着双手,嘴巴呷着黄连般苦涩地一张一合。被她瞪恼的春雪喝问:“你瞪谁呢?”毛豆战栗,从惊愕中清醒,撇着小嘴爬下床,光脚踩地的咚咚声深入毛豆奶奶的卧室,随之传来轻声乖哄和委屈的悲哭。
毛豆被呵斥之后的呆样与我儿时一模一样。
据毛豆奶奶所说,我幼年常遭醉酒父亲的恫吓、掌掴与踢踹,又总是目睹家中频起的纷争,所以在遭到粗暴对待时,会呆立原地、直勾地盯着对方。老师训斥我时总以为那呆瞪、是在挑衅,耳光、书本便劈头盖脸砸来。毛豆奶奶向老师解释,这是因我被父亲的喜怒无常刺激所致。然而,她在我脊背上砸断过几根抓挠、终日讽刺我鲁钝懒散的往事,她绝口不提。
自那事之后,春雪带头摧毁了由她自己建立的严格的育儿标准,对毛豆的需要渐渐漫不经心。我亦顺势躲清闲,除非妈妈、奶奶皆不理睬,毛豆才会蹭到我身边小声问:“一起玩?”若被拒,她便搂紧布娃娃“猫头”、叼着水壶蜷缩床头等待睡意降临。
直至上园,毛豆忽然在午夜频频尿床或呛水大哭,我们数日不得安眠、终日头昏脑胀,但她仍然拼命捍卫自己喝水入睡的习惯。那晚毛豆又大哭,我感到那道厉声劈中了墙面又连同混凝土的碎屑弹进了我的耳廓,刺得我耳膜生疼、嗡声阵阵。
我从枕上弹起,一连三个巴掌打在毛豆额角至后脑勺的位置,闻声赶来的毛豆奶奶打开灯,娃娃正坐在床上死死地拽着小背心尖叫,又拼命克制着自己哭嚎,两股剧烈顶撞的力量让她浑身颤抖、打着嗝抽噎,像只即将顶开盖的沸腾水壶。毛豆奶奶伸手要抱,毛豆直直地伸出胳膊,并拢五指拒绝了乖哄,独自吞咽着一切。
父母打孩子的动机无数,可理由只有一个,成人可以用暴力惩罚幼儿带来的不快,孩子无力反过来做。再厚重的爱也难抵这种不对等产生的肆意妄为,这是亲子关系的一层本质,其表现贯穿了我的童年,也终于在毛豆的生命中初现征兆。
想起之前,我陪着未满周岁的毛豆午睡,娃娃的柔软鼾声如煮沸牛奶的蒸汽氤氲在整个房间,小嘴、脸蛋、脑门肉嘟嘟地高高隆起,像只兰寿金鱼在温煦的日光中吐泡泡,我单手撑头侧卧在榻榻米上昏昏欲睡,毛豆抱着布娃娃咕噜一下滚入我的怀中,小嘴吧咂着发出“巴咕巴咕”的声音。那一刻,幸福的震颤似轰击,又似刺痛,我几欲垂泪。我想,我会爱这个孩子,会以与我父母完全不同的方式爱这个孩子。
我错了,爱孩子,同时保持对暴力的高度警觉也并不能让我成为一个好父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晚,毛豆拒绝大人乖哄的戏剧化姿态让我印象尤深,这种倔强显现出天生的内在力量。毛豆一定会比至今仍在童年泥淖中挣扎的我更加强大。
我努力温柔一些,毛豆坚强一些,我们的未来,会比我的过往更临近幸福,我如此希望,我这样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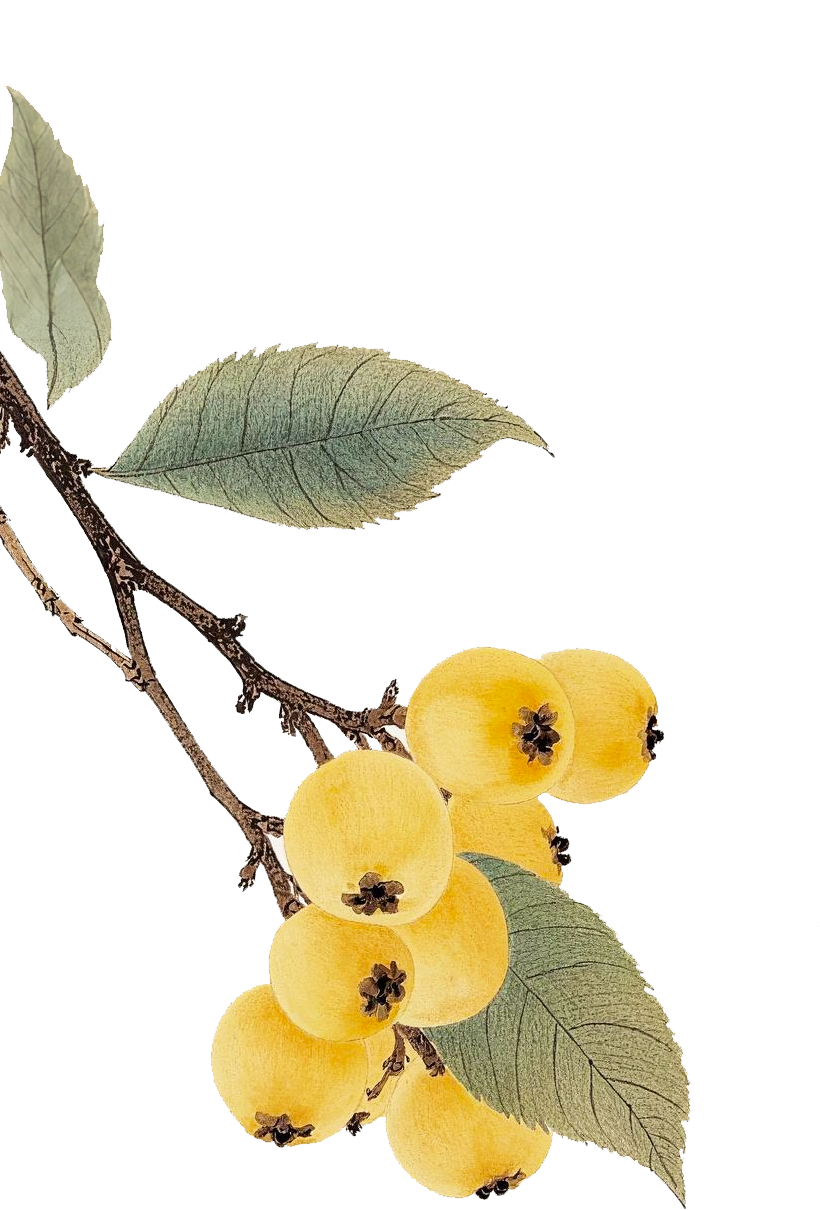
□李春
雨如精灵
焦渴了一个季度
相思的泪
冲破了浩渺的时空
跌落在思念的河床上
寒冬的那头
似曾有过飞逝的红颜
大地
苏醒了刻骨铭心的痴情
北方的初春
不喜欢烟雨江南的温柔
雨露桃花
撑开了素默的胸口
雨落春天
草也长
莺也飞
梦的花朵
悄然开放
所有的播种
都能芬芳吗
眺望田野
叩问汗水
携手阳光明媚的日月
种一片风光
秋日里
我们一起听蛙声连奏
稻花香里
笑挥银镰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黄韵;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