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姬卉春
秋天来了,悄无声息地漫过窗台。一阵凉风,几片落叶,天高了,云淡了,心底的故事也再次涌上心头。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秋天记忆。它或许是故乡的一片金黄,或许是旅途中的一阵凉风,或许是深夜的一缕桂香。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串联起我们与这个季节最深厚的情感联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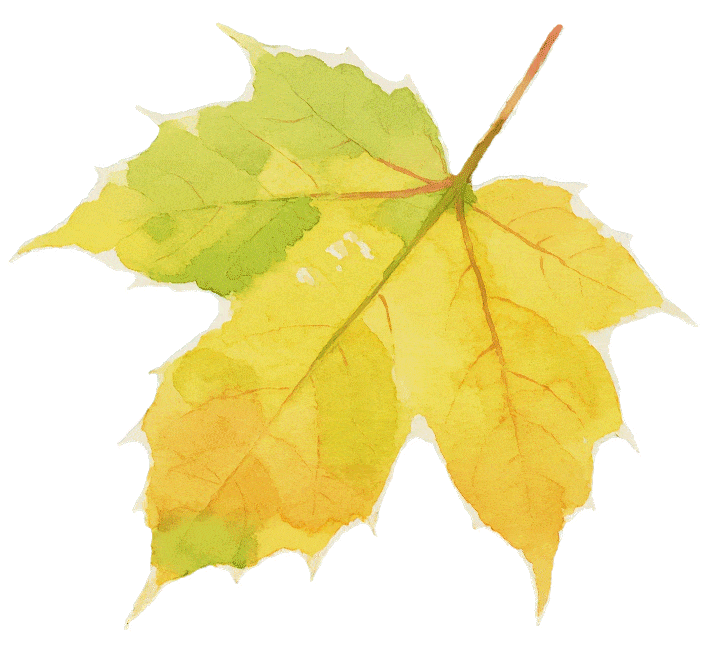
作者/高建军
北方的秋天总是那么短暂,你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它就与你匆匆擦肩而过了。儿时的记忆里,作为一个矿区,石拐大磁并没有什么特殊,灰与黑是它一年中大半时间的主体颜色。
身上的单袄已短得不成样子,这还是哥穿剩的,妈不知道从哪搞了些布,生生接长了一块,你还别说,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原装货。风顺着肚皮往里灌,让人觉得好冷。
“马儿呀,你慢些走啊,慢些走啊……”矿上俱乐部的大喇叭里,马玉涛还在唱,不用听我也知道,下一首歌一定是《泉水叮咚》。只要来了影片,俱乐部的喇叭里就会放这几首歌,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操本地口音的男人开始广播: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八点钟,今天晚上八点钟,我俱乐部上映最新故事片,最新故事片……
西山和东山是天然的回音壁,喇叭上的声音会很快被返回,并在这个不大的沟里形成回响。不管是东梁还是西梁,就是在羊场沟、冯家湾,你也会听得清清楚楚。
不过一年中也会有一两次例外,即使不放电影,喇叭里的歌曲也会响起,那就是秋天分菜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虽然大磁小得只有巴掌大,也同样沉浸在统购统销的氛围中。趁着太阳光还充足,各家早早地就把腌菜的大缸洗涮干净,让太阳进行最后一次消毒。余下的工作,就是用足够的耐心等矿上通知多会儿分菜。
喇叭一大早就响了起来,不用问,今天晚上,拉菜的车一准能回来。爹把绳子、麻袋拿出来,细心检查了一下绳子的结口,并用力拽了拽。
各家早早吃了晚饭,三三两两往俱乐部门前涌来。有些女人生怕男人们粗心大意,尽把一些帮子菜背回家,抱着还吃奶的娃也跟了来。
几盏大灯把俱乐部门前照得通明。大家伙把麻袋裹在一起,用绳子一绕,顺势往屁股底下一垫,再划拉过一个小石子,就在地下做起计划来。其实,这些数字早在家里就盘算过,现在,只不过用它来打发时间。“萝卜,50斤;长白菜,200斤;葱,30斤;圆白菜,150斤;土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可是一冬天全家的主要副食品,不算精细点,没等开春,就得喝西北风。当然,也不能太多,要不人家都吃上新菜了,自家还在烩酸菜。再说一进五月,酸菜就开始发软发臭了。
不知谁喊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拉菜的车回来了!”人群躁动起来,刚才还在抽烟的男人们,赶紧在鞋底上把烟火拧灭。
几束灯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司机们故意卖弄起来,把发动机的声音搞得好大,颇像刚刚渡过敌人封锁线的英雄。几辆车鱼贯而入,一字排开。车上几个跟着去装菜的人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家人,把自己在菜地里提前挑好的菜悄悄运出去。人们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人家辛苦了好几天,得些好处也是应该的,谁还没有点儿私心呢?
几个带轮儿的大秤很快被推了过来,大伙儿自动排成一排,听着管事的人喊自己的名字。
称的称,记的记,抬的抬,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彼此搭把手,跟着把过了称的菜抬下来。还没到半夜,已经分得差不多了,坡坡上、沟沟里,到处是星星点点的光亮,那是各家“运菜大队”照明的手电……
几天后,酸菜已经腌过来了,蔓菁、芋头也差不多有味道了。女人们会破例买上一块豆腐,踮着脚跑回家,做今年的第一顿烩酸菜。虽然舍不得放油,但酸菜的清香还是飘荡在空气中。
有的人会一边吃着烩得稀烂的酸菜,就着黑面的馒头,不住口地夸:今天的菜还行哩,好吃的,哪如再买一些放着来!也有人一边吃一边破口大骂:XXX这个灰个泡,尽给挑了些菜帮子,吃得他爷腮帮子还疼哩!
于是,这种被盐和水的混合物浸泡过的东西成为家家户户整个冬天的唯一,就是那些盐汤儿也不浪费,会被浇上些扎蒙油做成吃莜面的汤料。
等一缸缸腌菜在抱怨与无奈中逐渐见了底,仿佛就在一夜间,辣麻麻就成片地冒出了尖……
春天就要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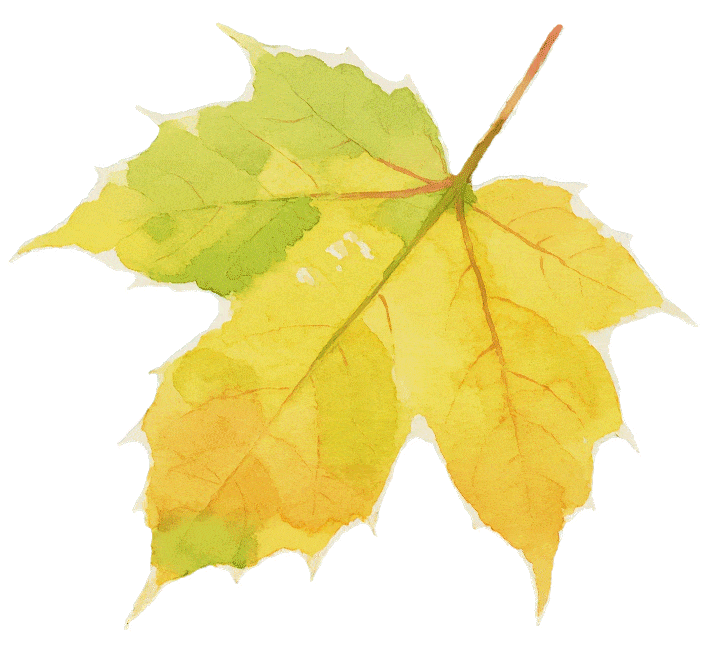
作者/周涛
八月的一个周末,几位文友从包头出发,沿固阳大道前往达茂,近两小时车程中,群山丘壑间的草木色彩交织,如流动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
首站抵达套马沟,景区内草木浓绿、繁花遍野,阳光洒落花叶间形成点点金斑,城市喧嚣被隔绝在外,只剩清脆鸟鸣。按当地文友指引,我们沿步道向德诚塔山顶进发。
登山途中,粉白、淡紫、嫩黄的花遍布山野,连石阶缝隙中都有小花点缀。民居外墙爬着青藤,回廊挂着村民自晒的干花,与鸟鸣相映,竟与我们的文创小院有几分相似。这里花是绝对主角,木质凉亭檐角、石制座椅扶手旁皆有盆栽,有一种紫色喇叭状小花,散发淡淡甜香,蜜蜂停在花蕊上随花枝摇曳。城市积攒的焦虑在此刻被花海滤去,只剩对自然的纯粹欢喜。
途中遇见挎竹篮采野菊的大嫂,她告知野菊可泡茶、填枕助眠,还提及“德诚塔”名字的由来,承载着套马沟人“以德为先,诚信为本”的百年信条,让我们明白此处之美不仅在花草,更在代代相传的生活准则。
登顶后,漫山野花如彩色绒毯铺向远方,远处马群飞驰,原是赶上国际马术耐力赛。文友介绍,远处村史馆藏着套马沟过往,“红旗渠”见证村庄变迁;近处九曲黄河阵满含民俗浪漫,采摘园蔬果鲜嫩。
下山后,我们寻到长寿井,井水清冽,映着云影。穿过风车隧道,彩色风车转动的影子如跳动的音符。在套马沟农庄,乡村焖面香气扑鼻,青椒、土豆、豆角等食材裹着酱汁,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
午后驱车奔腾格淖尔,沿途不时停车赏景:蹒跚学步的牛犊跟着母牛觅食,骏马在坡上悠然甩尾,成团的白云如草原长出的棉絮,温柔美妙。
傍晚六点抵达腾格淖尔,“腾格淖尔”意为“天之湖”,是艾不盖河的尾闾湖,曾干涸30年,去年下半年才恢复水流。牧马人停下告知,前年还能在此捡干蚌壳,如今水边草已没过马蹄,开春还有天鹅落脚。风携水汽掠过,让人真切体会到“自然的韧性”,这是草原与河流间“你未放弃等待,我便不负奔赴”的动人约定。下到湖边,水色因泥沙呈浅黄,文友脱鞋戏水,远处野鸭嬉戏,还有人家在野炊,烤肉香与湖水湿润气息交融。
返程路过查干哈达苏木,夜色中前往“天边草原自驾游营地”。营地院落空旷,五顶蒙古包如草原长出的大蘑菇。晚餐在蒙古包内,清炖达茂羊肉仅用盐提鲜,烤羊肉包子外皮酥脆。蒙古族主人介绍,羊肉来自自家牧场,羊儿夏秋吃野花草料,蒙古包壁上的羊毛毡是老法子擀制,冬日保暖。
夜晚入住蒙古包,毡毛气息混着草原潮湿,别有烟火气。天窗上,夜空繁星如碎钻。我们在蒙古包外铺气垫床观星,耳边是草叶沙沙、虫鸣唧唧与心跳声,野猫亲昵呜咽。忽有闪电,大雨倾盆,雨点砸在蒙古包上,节奏安心,比“雨打芭蕉”更显平静。
次日清晨,推开门便是层次分明的草原,如晕染的油画。小菜园里,黄瓜、西红柿、辣椒沾着露水,生机勃勃。
返程顺道去敖伦苏木古城,途中遇“雨界线”,抵达时雨停。古城荒草没膝,露水沾湿裤脚。我们走进荒草,登上旷野高台,指尖抚过残破石壁的纹路,发现砖缝中一块带蓝白釉色的元代磁州窑陶片。文友介绍,这里曾是丝绸之路北线上的重镇,元代为成吉思汗“驸马府”,明代是阿拉坦汗避暑行宫,“敖伦苏木”意为“庙宇众多”,曾是多宗教共生、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闭眼仿佛能见昔日繁华,如今只剩残破高台诉说过往。
沿南边墙行走,城门、瓮城基础清晰,石臼、陶片散落,艾不盖河如哈达蜿蜒。文友说元朝兴起成就了古城辉煌,我却认为是艾不盖河滋养了它。离开时雨又落下,望着雨雾中的高台,猜想古城消失或与河流干涸有关。
两天行程落幕,驶离草原时,德诚塔的信条、牧民谈天鹅的自豪、古城的陶片、草原的星空雨声涌上心头,让人真正懂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这绿水青山是美景,是牧民的家园,更是达茂的灵魂与依托,为远道而来的人们提供了安放心灵的栖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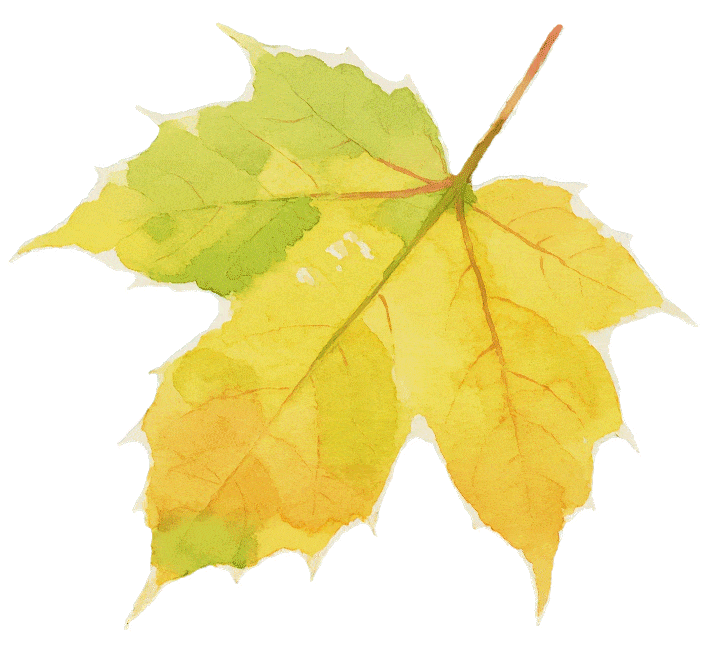
作者/张荣
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个秋天,院子里的老榆树叶子刚刚泛黄,秋风吹过会有几片落下来,轻微的簌簌声若有若无,就像他的悄然离去。其时,他91岁,我女儿口齿不清地对邻居们说:“我老爷爷死了,我们要搬家了。”
我坐着公交车赶了几十里路回去时,院子里,20年前就已经备好的棺木,像一艘小船停在那里。依然簇新的黄漆在午后阳光里刺着我的眼。
一起走过三十多年的岁月,他一直都像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他闭着眼睛躺在大炕的一角,任我们吵翻天都一声不吭,偶尔的制止也会被我们当成耳旁风。
他三岁丧母,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疼爱,包括自己的孩子。每每讲到他的性格,奶奶总会很生气地加上一句:“那样的石人。”
我12岁那年,他72岁,那年,他陪我来城里的大伯家读书。初次离家,他成了我想家时唯一的寄托。每天放学若看不见他戴着能遮住半个脸的老花镜在阳光里读书,我就会不停地问,我爷爷呢?虽然他仍是不大说话的“石人”,可看见他我就很踏实。
他给我铺床叠被,给我打洗脸水,催我早早起。每隔一段日子,他还背着大伯家的两个弟弟偷偷给我几毛零花钱。如果我们姐弟之间有什么不愉快,他一定会瞪着眼睛训斥他俩。许多时候,房间只有我们俩,我在地脚的小桌上写作业,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木床栏边读书。因为从小读的是私塾,他读书时喜欢出声,但简化的汉字他并不熟知,遇到不认识的字有时就直接用“什么”来代替。后来我们姐弟三人遇到不认识的字都会模仿着他的陕北口音互相问:“这是‘什么’?”然后笑得前仰后合。
暑假前夕,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车费,他早早就催着大伯去联系能回家的顺路车。那个七月的清晨,我们祖孙二人归心似箭似的爬上了高高的、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的大卡车。碧绿的原野上,金色的麦浪,起伏的瓜田,向日葵开成一道金黄的绸带萦绕在青山绿水之间。因为车速飞快,酷热的夏季风变得清爽柔和,挺拔的白杨在风里翻出银白的背面,是一朵朵银色的大花,在明晃晃的阳光里闪着晶亮的光,轻盈的白蝴蝶一双双从我的头顶飞过。此后,我再没有过那样的旅行,也再没见过那样美丽的夏天。
那个秋天,我升入初中,他不再天天陪着我,闲不住的他开始做起了小买卖,用自己挣的钱给我们压岁钱。他这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成功的商人,可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农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老了,银白的头发一天天稀少,听力一天天减退,腿脚一天天迟钝。奶奶去世那年,我有了女儿,妹妹远嫁京城,我们不再唏里哗啦去开他的屋门,不再莫名其妙地在他的午睡时间大笑,他依旧在阳光里念念有声地读书,寂寞地在房间里等着吃饭。有书看,我以为他不寂寞,我先生每次回去,总要陪他抽支烟,聊一会儿。每个年节,我们都回去时,他会一个个仔细盘问一番,快乐地陪我们笑,其实,他也是爱我们的,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2002年秋,90岁的他病倒了,从此不能再读书,就那么躺着等我们送来一日三餐。遇上我给他送饭,总要找些话题问他,他却总是沉默。时隔一年,他毫无征兆地离开了我们。爸去送午饭,他说不饿只吃了几口就躺下了,然后就走了。都说91岁去世算是喜丧,我们都没怎么哭,三天后,他被葬在后山的高坡上。他下葬十天后,爸妈离开住了20年的城郊旧居来到城里。
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有一种幸福就是能拥有健康的爷爷奶奶,尽管爷爷有时有点儿“石人”。但随着他的离去,我彻底失掉了这样的幸福。
又是一年秋叶黄,淡淡的微风拂过柳枝,我独自在灯下回想和他一起生活的30年,他的白发、灰布衬衣、黑框的老花镜、青筋暴露的手。再也听不到他陕西府谷的方言、琅琅读书的声音和偶尔唱给我们的歌。原来他一直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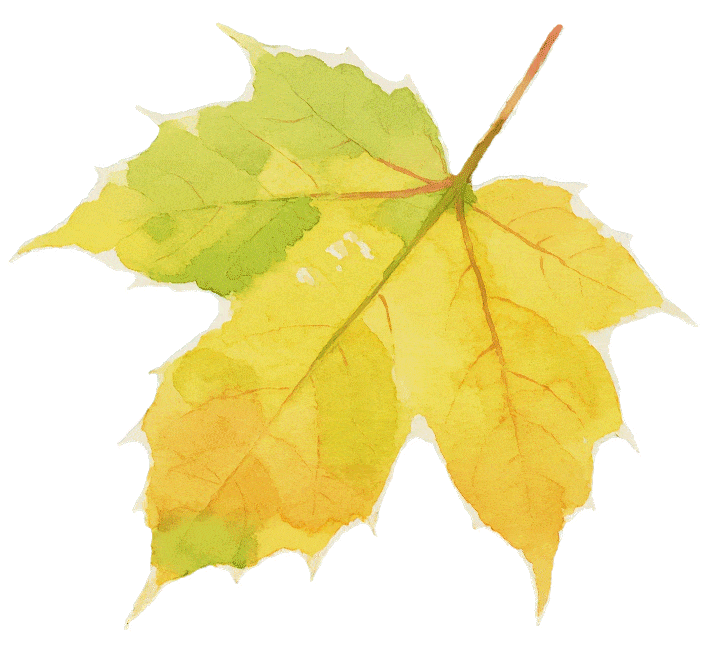
作者/吴尚晔
秋日,行人裹紧外套,步履匆匆。风卷起几片枯叶,在水泥地面打着旋儿,最终被扫进环卫工人的簸箕里,如同季节被扫进记忆的角落。人们习惯在秋天感怀凋零,叹息消沉——仿佛这季节唯一的馈赠便是万物偃旗息鼓的退场。然而若肯俯身细察那些看似衰败的深处,便会惊觉:秋日的消沉并非终点,它正以无声的坚韧,为遥远春天铺设着夯实的基石。
金黄的银杏叶被堆积在树根周围,如一层厚实温暖的绒毯覆盖大地。这并非无意义地消逝,树叶脱离枝头,不是仓皇地逃离,而是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它们将在寒冷与湿气中悄然分解,化作黝黑的腐殖质。每一片飘零的叶子,都在以自我消解的沉静姿态,为泥土注入养分,默默滋养着来年春天将破土而出的新芽。衰败在此刻正以最谦卑的方式,履行着对生命最深沉的承诺。
我们习惯将秋天浪漫化为“金秋”,仿佛它只是一幅由暖色调构成的风景画。但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秋天的本质是消逝。那些被我们赞美的金黄叶片,实则是树叶在死亡前最后的绚烂。植物学家告诉我们,随着日照时间缩短,树木停止生产叶绿素,原本被绿色掩盖的黄色胡萝卜素和红色花青素才得以显现。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美景”,本质上是植物面对死亡时的生理反应。这种认知颠覆了传统审美——我们赞美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消逝的过程。古代文人似乎比我们更早洞察了这一点,杜甫在《登高》中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木与江流的对比,是个体生命的短暂与自然永恒的残酷真相。秋天之所以能引发千古共鸣,正因它触动了人类心灵深处对时间流逝的集体焦虑。
在赛汗塔拉城中草原,我见过一群孩子收集落叶的场景。他们不是简单地捡拾,而是为每片叶子赋予故事——这片是蝴蝶的翅膀,那片是小船的帆……艺术家草间弥生曾说:“艺术是对死亡的抗争。”同样,我们对秋天的种种诗意诠释,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摄影,都是试图为必然的消逝赋予意义的努力。这种努力不是虚伪的掩饰,而是人类精神的崇高体现——明知万物终将凋零,仍坚持为过程赋予美与价值。
在村边开辟的小小菜园里,一双双皲裂的手耐心翻整着土地。他们将枯败的豆藤、瓜蔓仔细埋入泥土深处。“沤烂了,就是开春的好肥料。”他们抬起头,脸上沟壑里盛着秋阳,粗糙的手拍打着微凉的泥土,仿佛在抚慰一个即将沉睡的孩子。在这看似萧索的休耕期,大地正悄然积蓄着能量,如同伏笔埋入纸页深处,静待着被春雷唤醒的时刻,穰穰满家,岁稔年丰。
秋日的消沉,原是一场盛大奠基仪式的序曲。生命的智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从不在喧嚣的盛放中透支未来,反而懂得在看似停滞的休整里,为下一次的绚烂积累最深沉磅礴的力量。每一片落叶的飘零,每一粒种子的沉埋,每一寸土地的休憩,都非陡然的消亡,而是以退为进的深沉智慧,是生命在寂静里完成的能量转移与储备。
我们习惯于讴歌春天破土的锐利与夏日的繁茂葱茏,却常常忽略秋日这无声的奠基时刻。当城市的霓虹掩盖了星辰,当供暖的恒温模糊了季节的界限,我们是否也钝化了感知这种深层生命律动的能力?那在寒风中飘零的落叶,那在冻土下酣睡的种子,那在休耕期默默转化的养分,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往往孕育于沉寂,最宏大的序章常常书写于看似停滞的空白。
走出公园,暮色渐浓。我再次凝视那些堆积在树下的落叶,它们如此安然地躺在泥土上,透出一种沉静的责任感。它们消沉的身影之下,正悄然进行着一场关乎复苏的奠基礼。在这片北疆土地上,在这肃杀又孕育着希望的深秋,万物正以其深沉的静默,为那必将到来的春天,打下最坚实、最温暖的基奠——那关于生命轮回中最深邃的智慧:有时,真正的生长恰恰始于一次深刻的“消沉”。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