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风酿雪,岁序将新。冬日的街巷里,烟火揉着年味漫开。 这一页笔墨,是冬的诗行,也是年的序曲,愿你在文字里接住冬日的温柔,也揣着期许奔赴下一程山海。
——策划 姬卉春

作者/董利峰
冬天来了。想当年,土默川上的村庄里,酸菜、土豆是饭桌上最主要的蔬菜,十顿饭里八顿有酸菜的影子。要是没了酸菜,人们嘴里就会寡淡无味,整个冬天的幸福指数就要大大降低。
不知哪位老祖宗发明了冬天存储蔬菜的办法,反正从我记事起,腌酸菜就是家里顶顶重要的事了,就像土豆要窖藏,大雪前后要杀猪宰鸡,年前要大扫除,是刻在日子里的规矩。所以一到深秋,村里的主妇们就把耳朵支棱起来了,一听到巷子里有“白菜——,大白菜来——”的吆喝声,就赶忙放下手里的营生欢欢儿地走出院门,扯着嗓子喊住卖菜的,一群人围着菜车,对白菜叽叽喳喳一顿评头论足,讨价还价。那时腌酸菜要用青帮的顺直的没有油汗的大白菜,不像今天那种团团圆圆的抱头白。挑选好了,便称上二三百斤,小山一样堆在自家院里向阳的地方,先晒它几日,去去水汽,水汽太大容易腌坏。
要说能腌的蔬菜挺多的,比如黄瓜、芥菜、萝卜、芹菜等等,都和白菜一样既便宜又有营养,可这些菜腌酸了只适合做咸菜,只有大白菜腌酸了才适合做主菜,需求量比较大。
腌酸菜可有讲究了,得在深秋到初冬时节。太早,天气热,酸菜容易坏,太迟,白菜会冻坏。腌的时候,得掌握好盐的分量,盐太多,酸菜齁咸;盐太少,酸菜容易腐坏。腌得好的酸菜是金黄金黄的,味道酸脆爽口,连腌汤都清清亮亮。
我妈是腌菜好手。选个大晴天,妈妈坐在小矮凳上,右手捏着菜刀,左手按着白菜,坏叶、枯叶“簌簌”往下掉,眨眼工夫就把白菜收拾得顺直又洁净,然后“咔嚓”一声劈成两半——这样往后吃的时候,捞半棵就够一顿的。姐姐负责把修理好的白菜清洗干净,洗过的白菜放在蛇皮袋子上控水。我是搬运工,负责把白菜从妈妈这儿搬到姐姐那儿,顺便蹭个白菜心吃,白菜心真好吃,甜丝丝水泠泠的。洗净的白菜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安安静静,像在等待一场重生。
之后就是装缸。半人高的粗瓷大缸家家都有几个,装水,腌菜,储粮,放年货,存猪肉等等都离不开它。妈妈站在大缸边,把姐姐递过来的白菜一层一层紧紧实实按在缸里,每码一层,撒一次粗盐。此时,妈妈的眼和手就是最标准的秤,眼里看见多少白菜,手里就撒出适量的盐。所以,这个环节非妈妈不行。白色盐粒“沙沙沙”掉进缸里,钻进白菜的缝隙里,逐渐将白菜驯服。渐渐地,大缸满了,妈妈把一块早已洗好的大石压在菜顶上,腌酸菜工程终于告一段落。尽管手皴了腰酸了,可心里却是满足的、幸福的,充满期待的。
沉甸甸的大石把白菜的硬气一点点压下去,压出多余的水分,压出它们最后的一点骄傲,逐渐服帖、顺软,十几日后,所有的白菜获得新生,变成了酸菜。
于是酸菜以不同的样子开始了它的美食之旅:烩酸菜、酸菜汤、酸菜炒粉、酸菜饺子、酸菜包子、酸菜焖面等等。那时物资不丰富,不管你想不想吃酸菜,饭桌上都是酸菜。我的味蕾在酸菜里浸泡久了,那味儿就长在了记忆里,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只要有阵子不吃,就开始思念。闺女、外甥不爱吃,大概是没被这酸菜的香浸润过童年吧。
在杀年猪之前,酸菜里的油水少之又少。我们家最常吃的是烩酸菜。先用少量猪油把调料炝锅,然后加水开始熬煮切成大块的土豆。千万不能把土豆和酸菜同时下锅或先煮酸菜,酸菜的酸会让土豆硬挺,无法释放土豆的绵沙本质。得等先入锅的土豆快软烂时,再将切成细丝的酸菜放入锅中一同熬煮。半小时后,烩酸菜出锅了,酸菜的脆、土豆的沙混合在一起,别提多好吃了。偶尔家里会改善生活,烩酸菜里加一些豆腐或一些自制农家土豆粉,就更好吃了。等到杀了年猪之后,烩酸菜就升级了,成了杀猪菜、排骨烩酸菜,那独特的味道,光想一想,就叫人流口水。酸菜和猪肉简直就是绝配:酸菜以它被压制后的傲人的酸,分解化掉猪肉的油腻;而猪肉的鲜香,又能把酸菜驯服得更软和。经过大火的熬制,两种食材慢慢融在一起,最后完美契合。出锅的烩酸菜是和谐的、温润而柔和。这样的味道深深植入每一个土默川人生命的最深处,每当冬季来临,总忘不了腌酸菜。
现在的宴席上有一种大菜,也用到了酸菜。这是一种小火锅。最上面是肥瘦相间的扒肉条,下面是酸菜粉条。先吃一口烂到失魂落魄的肉,再吃一口清爽的酸菜,无比鲜香,我认为这是烩酸菜的另一种版本。酸菜还可以和羊肉搭配,热腾腾的火锅,涮完了羊肉,再涮上一些酸菜丝,鲜美到了另一个境界。
现在物资丰富了,一年四季想买什么蔬菜都有。到了冬季,人们再也不会储存大量蔬菜过冬,也不必忙活那么多年货了。那些曾盛满烟火气的粗瓷大缸,被孤零零地置于屋角,落了厚厚的灰尘,结了密密的蛛网,再也听不到码菜时的沙沙声、压石时的沉坠声。可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腌酸菜的习惯总也改不掉,只是再也没有过去那样一腌二三百斤的豪迈了。城里人住进了楼房,没了放缸的地方,老人家们便寻来小桶、玻璃罐,腌上两三棵白菜,聊以慰藉。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摆着袋装酸菜,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或许是少了深秋晒菜的暖阳,少了妈妈码菜时的专注,少了粗瓷大缸里酝酿的时光味道。
如今再吃酸菜,烩炒炖煮还是旧日做法,可总盼着能像小时候那样,踮着脚掀开缸盖,捞起一棵金黄金黄的酸菜,带着缸里清冽的酸香。那是土默川冬天的味道,是童年的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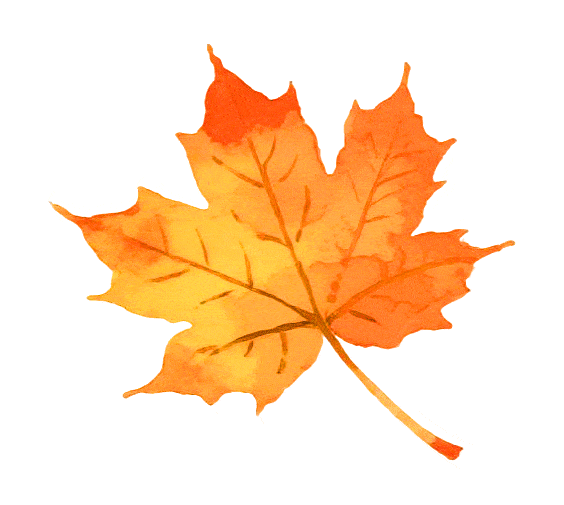
作者/张亚萍
汽车平稳地行驶在乡间的公路上,车轮碾过路面残留的薄霜与碎石,发出细碎又绵长的咯吱声。路两旁的树木褪去了所有绿意,只剩干枯的灰褐色的枝干一排排、光秃秃地矗立在寒风里,透着几分苍凉,也藏着几分沉静的力道。田野间铺满了枯黄的野草,风一吹便轻轻摇曳,零星几处裸露的褐色土地与枯草交织,辽阔苍茫得望不到头。这便是北方农村冬季最寻常的模样,苍茫寂寥中,藏着独属于大地的雄浑与厚重。
今日的天气格外慷慨,天空是澄澈得晃眼的蔚蓝色,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偶尔飘着几缕淡淡的云絮,轻轻浮在天际。太阳暖暖地照在车窗上,将它的光芒漫进车厢,不仅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也给冬日增添了几分慵懒又惬意的温柔,让这场奔赴多了几分暖意与期待。
我们几人是要去海子乡兴地村的朋友家,赴一场冬日里最隆重的邀约——吃今年冬天第一顿杀猪烩菜。对于村里人而言,杀猪这天邀上亲朋好友上门帮忙,围着灶台炖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肉烩酸菜,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也是冬日里最热闹的盼头。大家聚在一起,不光是为了贪恋这一口肉香裹挟着酸菜鲜香的地道滋味,更是庆祝一年劳作的圆满,犒劳自己与家人一整年的辛劳与坚守。
驱车进村已近中午,大铁锅里的酸菜与猪肉早已冒着咕嘟咕嘟的热气,散发出阵阵肉香与酸菜的鲜香。女人们在灶台边忙碌着,杀猪烩菜之外还准备了凉拌豆芽、豆腐丝、猪肘子、猪肝、猪耳朵拌黄瓜等好几个凉菜。
朋友家的院子非常大,从正房到南房足足有六十米。院里铺着小块青方砖,平整又扎实。靠东墙搭着简易鸡棚和鹅棚,五六只大白鹅摇摇摆摆地边踱步边嘎嘎嘎地叫着,七八只土鸡在宽阔硕大的院子里自由自在地溜达着,时不时咯咯轻啼,偶尔落下几摊鸡粪和几片淡淡的绒毛。一只大黑狗对着我们汪汪叫着,尾巴却不停地打转,透着几分警惕又热情的模样。这样一幅烟火氤氲、鸡犬相闻的画面多么鲜活治愈、亲切暖心。明媚灿烂的阳光将小院裹在融融暖意里,站在这宽敞明亮的院中,望着澄澈蔚蓝的天空,心情也会变得明朗惬意起来。
朋友极爱唱二人台,这种刻在土默川人血脉和骨子里的乡土艺术,是藏在基因里的乡愁,是烟火日子里的诗意与欢畅,更是乡亲们茶余饭后、婚丧嫁娶都离不开的精神慰藉。今天受邀赴宴的足有二三十人,其中很多都是二人台的忠实爱好者和参与者,有常年在村里搭班演唱的老艺人,也有跟着长辈学唱的年轻人。开饭前,正房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便成了临时的二人台小戏台,大家轮番登台表演,热闹非凡。
乐队老师技艺娴熟、信手拈来,熟练地奏起了二人台经典曲调《走西口》《挂红灯》《画扇面》的片段,悠扬婉转的四胡,清脆明快的扬琴,高亢嘹亮的枚,熟悉亲切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把人带入了苍茫辽阔又醇厚绵长的意境里,让土默川的冬日烟火与乡音紧紧相拥。有人伴着旋律亮开嗓子,唱腔里带着土默川方言的质朴本真。有人一边唱一边轻轻摇摆身子,眉眼间满是投入与欢喜。台下的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拍手叫好,偶尔跟着哼唱几句,歌声、乐器声、喝彩声混在一起,与厨房里飘来的烩菜香交织汇聚,漫过小院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冬日里最动人的乡音盛宴。
猪肉烩酸菜端上桌了,酸菜是黄澄澄脆生生的酸香,猪肉是醇香浓郁肥而不腻的咸香,土豆是绵沙软糯的鲜香,这一碗地地道道的农家杀猪烩菜下肚,从舌尖到筋骨,全都充溢着踏实的满足和纯粹的欢喜。大家围坐在桌前,热热闹闹地品美食、饮美酒,愉快尽兴地聊着天拉着家常,席间还有几位姐姐即兴唱了几段山曲儿。山曲儿也是土右旗特有的传统音乐,这种艺术形式讲究现场发挥,唱词全靠现编,随口就能把杀猪宴的热闹、日子的红火唱进曲儿里,是调节现场气氛独具特色的重要形式。
宴席的热闹渐渐地沉淀为满足的慵懒,我们也踏上了返程的路。窗外依旧是那片苍茫的冬野,但此刻再看,那份寂寥中却分明能触摸到一种厚实的暖意,那是千百个类似的农家小院里,正升腾着的同样扎实热闹的生活气息。
这一顿杀猪烩菜,没有精致的排场,却有最真切的欢喜;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最滚烫的温情。土默川的冬日,正因这烟火佳肴、乡音乡情,才显得格外动人。


作者/张荣
母亲总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就买回下一年的日历,是一大本、需要每日撕掉一页的那种。
阴阳历的日期、星期、节日、节气等信息一应俱全、一目了然,让每个日子都过得明明白白。
童年时,我家的这种日历挂在一个泛黄的硬纸板上,这个纸板最初好像就是用来挂日历的,上方的正中间有两个小孔,下面的空白处有一幅插画,画着两个胖乎乎的姑娘,倒是和我家很搭。旧的日历撕完了换上新的,日积月累,这张纸板微微变了形,挂在墙上不再服帖,母亲就用一块透明的塑料板替换了它。
撕日历是祖母和母亲的事,而撕下来的这一页薄薄的纸,不是用来引燃灶火就是被祖父和父亲当成了制作卷烟的材料。我一直不大喜欢这种老式的日历,每天撕扯怪麻烦的,我唯一喜欢的是每年的最后一天换新日历的那一刻。母亲或是祖母郑重地从墙上取下钉日历的纸板,拆掉最后那一页,再把崭新的一厚本钉上去重新挂回墙上。新日历有一张喜庆的红色封面,通常被我要来玩耍,垫在放布娃娃的点心匣子里或者贴在结了冰花的窗玻璃上当窗花。
后来,每到年末,祖母的弟弟,我的四老舅,会从北京给我们邮寄一本挂历。祖母每年都会将这本她弟弟送给她的新年礼物转送给她的儿媳。我母亲就成了村里唯一屋里挂着挂历的主妇。那年月,挂历是稀罕物件,婶子大娘们来串门,总是恭敬地洗了手,凑到跟前一页页翻看。
挂历年年不同,以风景摄影居多,印象最深的是某一年的雷诺阿油画和1988年的“范曾近作”,不被婶子大娘们喜欢的这两本,正是我喜欢的。我喜欢雷诺阿油画不是因为我有艺术欣赏能力,吸引我的是画面上可爱的卷发洋娃娃和少女衣领上的蕾丝边,而挂着“范曾近作”的那一年,我们举家搬迁至包头城郊。
此后,挂历渐渐地不再是稀罕物,四老舅也没再寄新挂历来,而“范曾近作”作为我家最后一本挂历一直在新居门后面的暖气管子上挂了多年。
而我,就在日历的撕扯与挂历的更迭里悄然长大了。许多事,我忘了,我丢盔撂甲地忙着成长,风风火火地遗忘着时光。倏忽间,突然有一天,祖母走了。我刚怀孕时,还曾问她能不能给我看孩子,她说等孩子会走了就帮我带,婴儿怕是抱不了。两年后,祖父也突然走了。原来,日历一页页地撕,竟然也会撕掉生命。
2003年秋,祖父入土为安,父母随即搬离城郊居住了十余年的家来到我定居的城区。楼房的墙壁不好钉钉子,母亲就买了粘贴挂钩用来挂日历,好像城里的日子也是要一页页撕掉才踏实。那个挂钩贴在两个卧室之间的墙体上,是个小苹果的形状,如今房子租出去好几年了,偶尔进去看一眼,那个挂钩还在,只是,租客家不挂日历。
现在,父母和我同住一个小区,母亲的日历钉在一个台历架上,很结实的红色硬纸壳。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说:“今天是25号吧,忘了撕日历。”随即他撕掉一张扔进垃圾桶。我看见旧日历又剩下薄薄的几张,一年又要过去了。
母亲在厨房炒猪肝土豆条,每年的这个时段是老家杀猪宰羊的季节,刚刚过了冬至,阳光就好像多了些暖意,其实北方的极寒天气还在路上呢,我却无端地觉得春天不远了。
在冰凉的风里呼出一团团白气,在白茫茫的人迹罕至的雪野或盐碱地上奔跑,干枯的芦草在脚下发出折断的脆响,炒猪肝、炒瘦肉的香味从村子里飘出来,传得老远。
有时候,依稀觉得那样的时光并不遥远,怎么父亲就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母亲蹲起坐下的时候也透露出了艰难。母亲结婚后祖母主动让出家庭主妇的位置,凡事不再做主,祖母与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和睦的婆媳。我结婚后,母亲替我操心琐事,依旧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不是我不愿意承担,而是为了让母亲一辈子都有成就感。
在母亲家茶几下面的格子里,一本崭新的日历静静地躺着,随时等待上阵,这一年就要结束了。阻止不了时间的流逝,就珍惜每一刻的陪伴吧。


作者/姜雅静
每到新年,人们总是禁不住回望,盘点一年的得与失、乐与悲,我也一样。一人独处时,总会想这一年做了些什么,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于是,对明天、对将来的焦虑,像一只被吹胀的气球,在日历越翻越薄的日子里,愈发膨胀。
我这人,天生胆小。怕见生人,不敢走夜路,夜里不敢一个人睡,也从不看恐怖片。因为胆小,许多事便不敢轻易尝试,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就是最好的佐证。邻居家的孩子一有机会,就把大人的自行车推到空地上练习,而我却总蹲在原地摆弄脚蹬子,看着空转的车轮折射的光,便觉满足。不学自行车的原因很简单,只是怕车子会倒。也正因不会骑车,上学时,若非家人接送,便是自己步行前往。直到上了初中,学校离家太远,在父母的督促下,我才用一个假期学会了骑自行车。学车的过程还算顺利,在学校操场上没几天,就骑得十分熟练。可真正到了马路上,往来的人流车流,又让我望而却步:这么多车,我停不下来会不会撞到别人?需要拐弯时,旁人不让我该怎么办?诸如此类的念头,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推着自行车走。
我想,自己的焦虑根源,正是这份胆小。心胆怯弱,便难有安全感,总对未发生的事满心恐惧。夏天某日,天气预报说接下来几天都会有雨,尤其次日就会有暴雨。我听罢便深信不疑,还依照建议囤积了足够周末食用的肉菜蛋奶、面包水果,脑海里尽是窗外大雨倾盆,我窝在家中安然吃喝的温馨画面。结果等了一整天,不仅没下雨,还是个艳阳天。夜里出门散步,望着漫天晚霞,我暗自检讨自己的过度敏感。可在这件事上,向来善于总结的我,却没能“吃一堑,长一智”。入冬后的一天,主持人预报市区会有降雪,我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早早就开车出门。一路上,分不清是天色昏暗还是阴云笼罩,只觉空气湿冷得像是要落雪,还暗自庆幸赶在降雪前到了单位。谁知刚出电梯,一轮红日便跃出楼宇的遮挡,洒下耀眼的光,像是在告知我又是晴空万里,又似在笑我一夜的心神不宁。
现代人的焦虑本是常态,究其根源,与信息过于发达脱不了干系。当然焦虑也分阶段,人生不同时期,焦虑的内容各不相同,而我现阶段的焦虑,皆源于年龄。行至知天命的年纪,心里忽然生出几分迷茫:想躺平,心有不甘;想有所作为,找不到赛道,对未来的焦虑也与日俱增。焦虑最甚时,我偶然读到这样一段话: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儿,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我没有深究这句话的出处,只觉它如穿透云层的一束光。
我买来《救猫咪》这类工具书,盼着有朝一日能圆了写小说的心愿;翻开季羡林先生的《心安即是归处》,感悟先生历经百年沉淀的生命智慧;品读汪曾祺先生的《食事》,于质朴的文字里,品味食物裹挟的人间百味。读着读着,内心也渐渐归于平静。
曾看过一期综艺节目,当代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那极具“破碎感”的人生,让在场之人无不慨叹。节目中,主持人问起老先生度过人生危机的方法,他只是淡然答道:往里走,安顿自己。谈及当年乘船在海上遭遇暴风雨的经历,先生感慨,应对人生的风浪与颠簸,唯有一个办法,便是从内心安顿自己。老先生的话语,让人恍然醒悟:生活从不必恐慌,只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便有勇气直面前路的风雨。就像当年学骑自行车,后来在同学的陪伴下,我终于敢骑着车在道路上穿行,那一刻,心底涌起“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与轻松。也如某个清晨,我被隆隆的雷声惊醒,匆匆驱车上班,终究还是遇上了大雨。收音机里的浅吟低唱伴着我,在雨幕中小心前行。行至单位附近,雨便停了,澄澈的晴空消解了雷暴带来的慌乱,仿佛一切波澜都未曾发生。
从现在起,做一个气定神闲的人吧。内心无忧无惧,纵使外界万般变化,依旧能不乱方寸。不再纠结过往,不再忧虑未来,安心活在当下。就像《漫长的季节》里那句经典台词:往前看,别回头!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