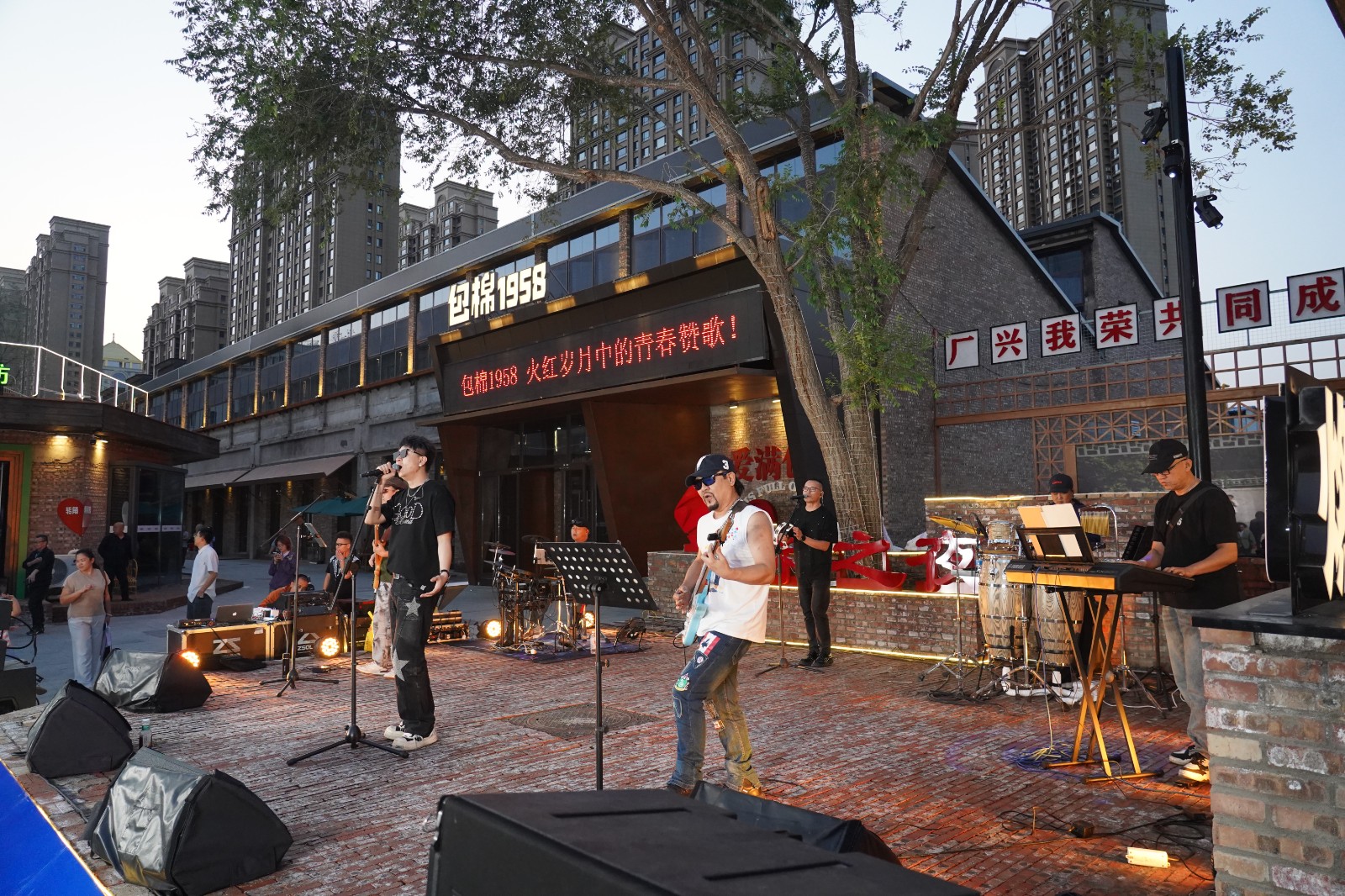黄河岸边秋意浓
作者/周静
我出生在黄河北岸一个小村庄,儿时的我从家出发,步行十几分钟,淌过一道水渠,便可站在高高的黄河大坝上。放眼望去,滔滔黄河之水奔腾着、咆哮着向东而去。岸边是长势旺盛的庄稼地,齐齐整整,深深浅浅。距离大坝不远处,是黄河南移时留下的一片清澈的水域,也是村民们到对岸锄地拔草、收割庄稼的必经之路。
秋收时节,村子里最是热闹。天还未亮,公鸡扬起脖子高声打鸣,圈里的猪呀羊呀饿得直叫唤。女人们早早起来,喂鸡喂猪,烧火做饭,准备干粮。炊烟从各家的烟囱里升起,在晨曦中交织成一幅朦胧的画。
一个晴空万里、秋风送爽的早晨,我和母亲拿着镰刀来到岸边,船上已坐满了十几位到对岸劳作的村民。待我们跳上船,船夫便解了绳索,划着木桨向河对岸驶去。晨光中,河面波光粼粼,蜻蜓飞来飞去。偶尔传来一两声水鸟的鸣叫,欢快而热烈。风儿吹拂着面颊,凉凉的,湿湿的。
片刻工夫,我们的船靠岸了。下船后,我和母亲前往我家那片田地。小路两边的庄稼地里,玉米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原本嫩绿的叶片已泛出淡黄,边缘微微卷曲,却仍紧紧裹着鼓胀的棒子。偶尔露出几粒金灿灿的玉米粒,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向日葵秸秆顶端那圆圆的葵花盘微微低垂着,花瓣已褪成火红与赭黄交织的色调,花盘上蜂唱蝶舞。沉甸甸的糜子穗儿弯着腰,微风拂过,荡起层层细浪。忽然一群觅食的麻雀从中掠起,原来糜子中央有个手拿木棍的稻草人,木棍上的彩色布条在随风摇摆。在我眼里,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这里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又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情,所以我打小就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还有一次,随父母去西南的河头地里收割玉米。路途遥远,又是骆驼拉车,虽稳但慢。早晨出发,傍晚才回家。坐在骆驼拉的木架车后面的我,摇晃着双腿,心里比赶集还高兴。仰面躺在车上,看云卷云舒,云的形状让我想象无限。翻过大坝,途经一湾水域时,看见一只渔船在水中轻轻摇曳。渔夫站在船头,手臂一挥,网便撒成一道银亮的弧线,慢慢沉入水中。鱼鹰低掠过水面,翅膀拍打时溅起细碎的水花,转眼又冲向高空,只留下一圈圈涟漪。远处的河滩上,羊群啃食着青草。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眼前的玉米秆挺立如林,像一列列士兵,等待着检阅。大人们将骆驼从车辕间解下。那牲口脱离了轭具,似乎也觉出几分轻快,却不嘶鸣,只驯顺地由人牵着,拉到田地尽头有草的空地,逍遥自在去了。大人们开始挥舞镰刀,将一根根玉米秆割倒。我跟在后面,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扔在地上,放成一堆。掰了大半天,总感觉应该快到地顶头了。可走出外面向前方望去,还是一片玉米林。玉米林里闷热极了,汗水从额头流到眼睑、脸上。蚊子满天飞,我一边挥舞手臂打蚊子,一边掰玉米,心想:这么大一片啥时候才能掰完呢。便偷偷溜出去,用小铲子掏土挖坑,在草丛中寻觅小小的鸟蛋。
一只蚂蚱蹦来蹦去,逮住它不费吹灰之力,捏着两条腿看它跳舞。摘一片细长的芦草叶子,放在两个大拇指中间使劲吹,却怎么也吹不响。往河里扔石头、打水漂,甚至把玉米粒儿剥下来一把一把丢在河里喂鱼。玩累了就回来继续掰玉米,掰累了就坐在玉米秆上,将玉米叶子撕开拉成长条编麻花辫……

夕阳西斜时,整个河岸都浸在暖融融的光里,连黄河水也泛着金色,仿佛流淌的不是水,而是熔化的铜汁。我们把堆成小山的玉米用箩头、袋子搬运到木架车上,四周和上面用玉米秆遮挡、覆盖,然后用粗绳子前后左右扎牢、绑紧,骆驼载着满车的玉米向家的方向走去。我坐在上面,双手紧紧地抓着绳子,生怕在颠簸的路面上被摔下去。经过那片水域时,一株株芦苇摇曳生姿,白色的芦花漫天飞舞,如雪花般轻盈美丽。
夜幕降临了,羊儿入了圈,饱腹的骆驼安静地卧在大门外。吃过晚饭的我,来到堆满黄灿灿的玉米棒的院子里,抬头看悬挂在天空中皎洁的月亮,柔和而又亮丽,隐约传来还未入睡的乡邻或高或低、絮絮叨叨拉家常的声音,乡村被一片温柔笼罩。
黄河、大坝、木船、金色的田野,那些封存在我脑海里的秋日美好记忆似黄河水久久流淌,时时回放。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