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在写大宛名马的《房兵曹胡马诗》中说:“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大宛名马的神骏跃然纸上。当战马的嘶鸣穿透历史烟云,当马蹄的声响敲击帝国命脉,那些曾经奔腾在中华大地上的名驹,早已超越了坐骑本身的意义。它们承载着帝王的雄心,见证着王朝的兴衰,甚至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农历马年即将到来,我们不妨来聊聊中国古代的名马,循着这些四蹄印记,走进那段马背上的中国史,探寻一匹马究竟如何载动一个庞大帝国的命运。
天马西来
汉武帝的名马执念
两千多年前的未央宫中,汉武帝刘彻正对着一张西域地图沉思。他的案前放着张骞带回来的奏报,其中一行字被朱笔反复圈点:“大宛有宝马,汗血,号天马子。”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仅看到了马,更看到了马背后广袤的西域、潜在的威胁与无限的机遇——那是一条足以牵制乃至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通道。
《史记》记载,当西域使者传来大宛有“汗血宝马”的消息后,这能日行千里、肩胛渗出鲜红汗珠的神骏就成了武帝的执念。其后,当乌孙国献上良马时,他兴奋地翻阅《易经》,援引“神马当从西北来”之句,先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但这远不能满足他对更高品级战马的渴望。
一场因马而起的外交风波就此上演。汉使车令携千金及黄金铸造的金马前往大宛,求换贰师城的汗血宝马。傲慢的大宛国王拒绝了,汉使愤而“椎破金马”,大宛则截杀汉使。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封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兵数万远征大宛。这场第一次远征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而惨败。但汉武帝不惜“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倾全国之力再度西征。三年后,汉军兵临城下,大宛贵族杀国王、献马求和。
当数十匹汗血宝马终于踏进长安城时,汉武帝亲自作《西极天马歌》。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表面为马,实则一举打开了汉朝经略西域的大门。
西极天马歌
汉·刘彻
天马徕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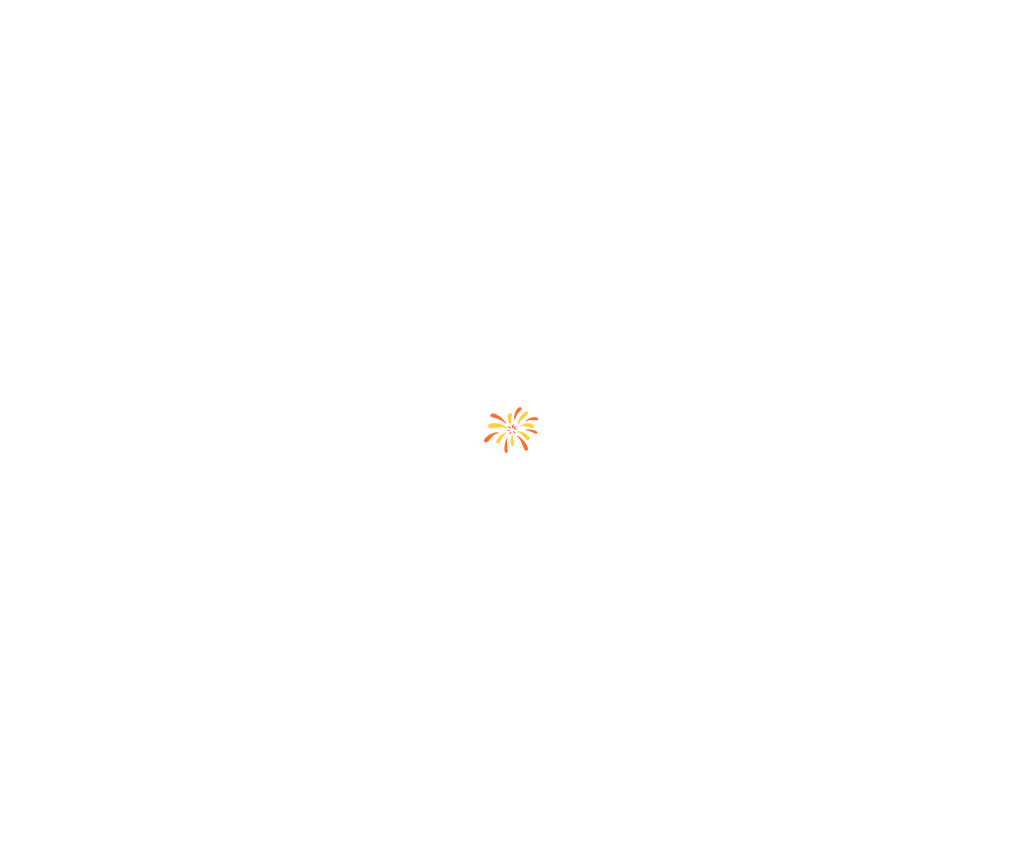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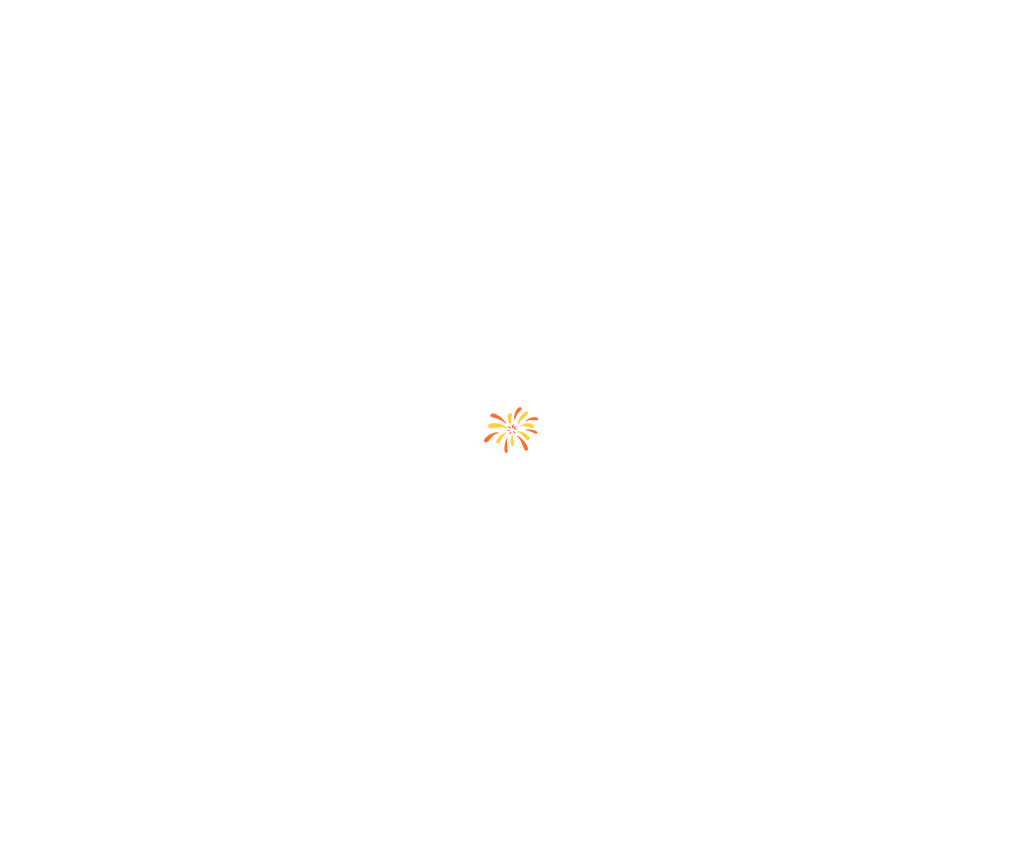
昭陵六骏
丝石刻上的帝国记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长安城外的九嵕山。这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北司马门内,曾矗立着六块巨大的青石浮雕——这便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每一块石刻,都是一段浴血奋战的往事。李世民曾为它们一一亲撰赞语,字字铿锵:飒露紫、拳毛騧、青骓、什伐赤、特勒骠、白蹄乌……每一匹都是李世民从秦王到天子的生死见证。
这些浮雕由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图样,无名匠人悉心凿刻而成。战马结实的肌腱、飞扬的鬃毛、中箭后依旧不屈的神态,被永恒定格于青石之上。这不仅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更是大唐开国武功的纪念碑——马背上打下的江山,终究以马的石刻来铭记。
然而,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让这批国之瑰宝饱受劫难。民国初年,国内文物贩子勾结境外势力,将六骏拆解盗运。其中,“飒露紫”与“拳毛騧”被粗暴切割,先被运至北京,意图售予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袁以石刻残损为由拒收,两骏后被美国古董商购得,远渡重洋,今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另外四骏在盗运过程中被当地民众发现并拦阻,虽免于流失海外,却已遭不同程度损毁。2010年,中国学者首次赴美对海外二骏进行三维数据采集;2017年,陕西文物部门借助数字技术,令六骏在屏幕上实现“重聚”。然而,实物归国之路依然漫漫——它们不仅是石刻,更是一段被割裂的民族记忆。每当我们在博物馆的复制品前驻足,那些残缺的痕迹仿佛仍在诉说:国家强盛时,骏马载英雄驰骋天下;国力衰微时,连石头刻的马亦难以保全。

“昭陵六骏”石刻 图片来源:明孝陵博物馆
长陵八骏
明成祖的马背江山
时间跳转到明永乐年间。北京昌平天寿山下,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享殿前,也曾矗立八座石马——长陵八骏。这显然是对唐代昭陵六骏的追慕与致敬,但每一匹石马背后,都承载着属于永乐朝的开国记忆。
据明代笔记《双槐岁钞》记载,八骏各有名号:龙驹、赤兔、乌兔、飞兔、飞黄、银褐、枣骝、黄马。它们随朱棣历经靖难之役的大小血战,每一匹都曾中箭负伤。
郑村坝之战中,龙驹中箭,由都指挥丑丑拔箭救马;白沟河血战中,赤兔中箭,都指挥亚失铁木儿护主换骑;东昌之围时,乌兔中箭,都督童信亲自拔箭救马……石雕虽无言,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却仍能想见朱棣如同当年的李世民一般,亲冒矢石、冲锋陷阵。马背上的伤痕,正是王朝鼎革之际刀光剑影的印记。
有趣的是,朱棣的坐骑中再现“赤兔”之名——这二字跨越千年,自三国至明代,始终是良驹的代称。八骏名中多含“兔”字,如飞兔、乌兔、赤兔,或许正暗合古人“骏马迅疾如兔”的想象。可惜的是,长陵八骏的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均不如昭陵六骏完整,它们静静立于十三陵的苍松翠柏之间,仍在等待后人更深入地解读那段“马背上的靖难”往事。
木兰秋狝
乾隆的马背政治

《乾隆皇帝射猎图》中的骏马 清 郎世宁
当历史步入清代,马的故事在乾隆朝演绎出集政治、艺术于一身的独特终章。
每年秋季,乾隆帝率众北赴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这并非仅是游猎,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展演。皇帝通过亲驭骑射,检阅满洲、蒙古子弟的武勇与忠诚,重申“国语骑射”的立国之本,以巩固边疆统治。马,在此成为维系帝国武统与民族认同的核心仪仗。
乾隆对骏马的钟情,更升华为系统的艺术创作。他命宫廷画家——尤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为代表——为御马绘制肖像。郎世宁以西洋写实技法捕捉马的形神,中国画家则辅以山水意境,共同创作出《十骏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等一系列作品。这些画作既纪实又颂圣,将良驹与帝王威仪一同铸造成视觉典藏。
至此,马的形象在乾隆时代完成了关键转换:从唐代昭陵六骏那样铭刻战功的“武功纪念碑”,转变为融会祥瑞、君主品位与“万国来朝”象征的“文化珍品”。随着冷兵器时代渐远,马虽逐步退出实战核心,却被乾隆极致的美学化与仪式化,最终凝固定格于《石渠宝笈》的典册之中,为帝王名马的千年叙事,落下一个浓墨重彩的收笔。
来源:《包头晚报》文化版
责任编辑:曹靖宇(见习);校对:黄韵;值班主任:张燕青;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