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的冬天,是刻在骨血里的凛冽与滚烫。朔风掠过街巷,窗棂凝起冰花;炉火旁的炖菜咕嘟作响;寒夜里的灯火温柔明亮。这一季,既有天地间的清旷辽阔,也有烟火里的温情绵长;既有踏风而行的洒脱,也有围炉夜话的安然。寒来有声,岁月无恙;时序更迭,暖意如常。
——策划 姬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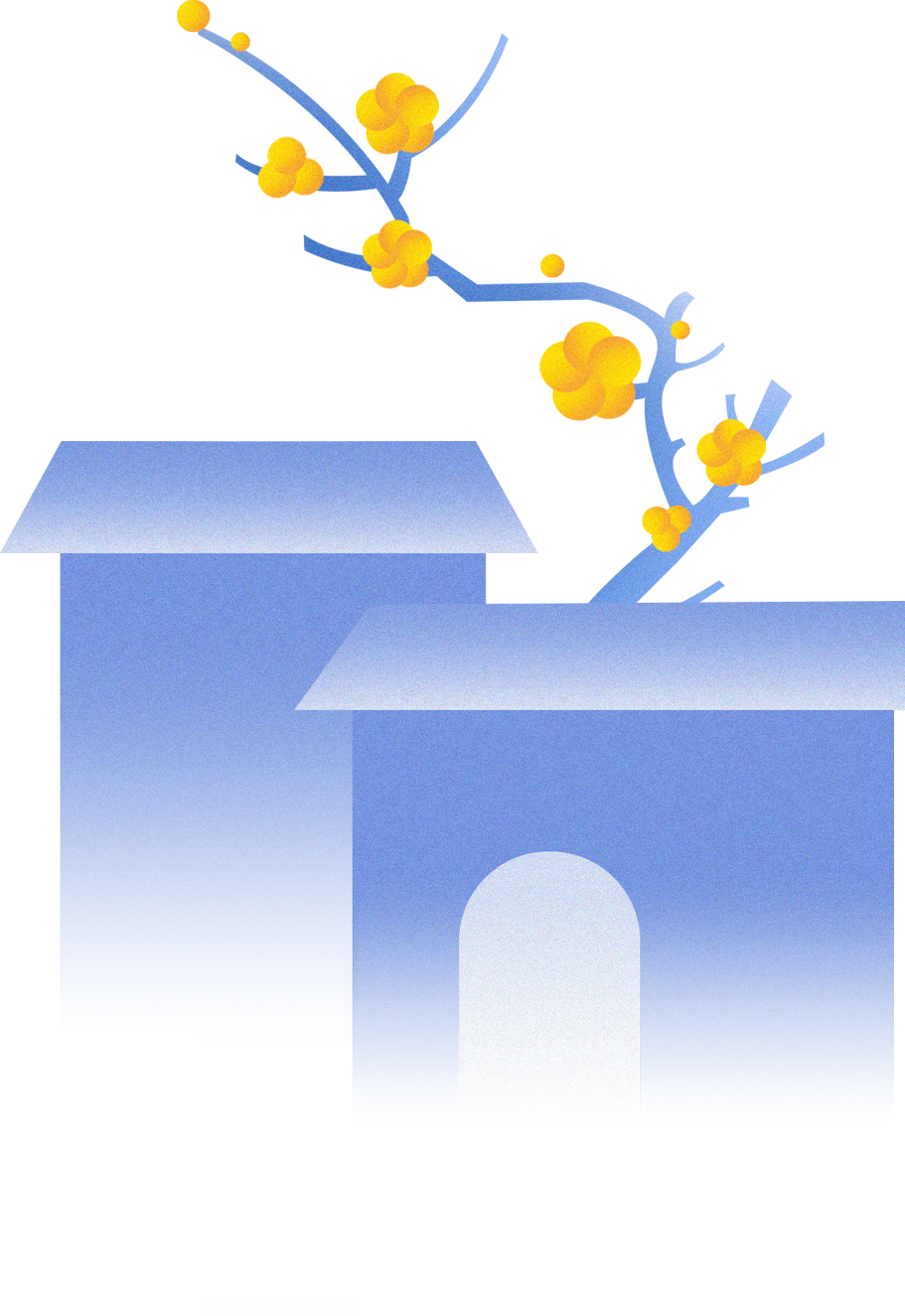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董利峰
一场秋雨过后,冬天的寒潮如期而至。路边的景观树在尖啸的冷风中瑟瑟颤抖,树叶上残存的雨珠被无情抖落,洒在行人肩头,敲打着湿漉漉的路面。路灯下,地面泛着冰冷的白光,不多的行人双手插兜,步履匆匆。我裹紧衣服缩着肩膀,也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家里的暖气已经供上,干燥的暖意顺着地板漫上来,看不见摸不着,却紧紧贴在皮肤上,没有烟火味,却足够熨帖。屋里的每个角落都被这恒定的暖意包裹着,无处不在。我舒坦地长叹一声。可这平稳的暖意里,总感觉缺了点儿什么——忽然想起从前,那些围着炉火取暖的日子,贫瘠却满是滋味。
那时,每个冬日的清晨,整个村庄仍在沉睡,天地间一片漆黑时,母亲便悄悄起身了。不一会儿,火炉“轰轰”地被唤醒,柴禾噼啪作响,火星偶尔窜出炉口,带着些呛人的烟味,火舌在炉子里欢快地跳跃。大灶上的水很快“滋滋”地唱起晨曲,氤氲的热气直冲屋顶,凝结在玻璃上变成缥缈的“白纱”,用手指一抹,能划出弯弯曲曲的痕迹,指尖沾着冰凉的水汽。我在母亲的催促中不情愿地起身,套上她提前烤得暖烘烘的棉衣,就着氤氲热气吃下两个荷包蛋,从身到心都浸着踏实的暖。背上军绿色的帆布书包,和邻居家的阿霞披星戴月,踩着冷硬的路面往学校走去。冷冽的空气追着我们跑,团团白雾有节奏地笼罩在嘴边,走着走着,白雾驱散了夜气,天色渐渐亮起来,薄雾像一层轻纱低伏在原野上。透过淡淡的雾气,能看见苍茫的原野,无边无际伸展到天边,看见原野上的坟冢与坟上高大的柳树,还能望见远处学校模糊的轮廓。
那所原野上的学校像座孤岛,四面八方的风都往这里灌,如同四面八方的小路延伸到校园。寒冷的冬季里,教室显得格外大,门窗总也挡不住寒风。虽然教室中间的火炉燃得很旺,却穿不透四处漏风的门窗,暖意在半路上就被冷气吞了。这火炉便是教室的“太阳”,“太阳”周围是热带地区,同学们穿不住棉袄,吵着要揭开炉盖。稍远些是温带地区,而四个角落和门窗边,便是寒带与极寒地带,那里的同学总在嚷着加炭。我的手被冻得蜷缩着写不了字,笔尖划过作业本时留下的是扭曲的“毛毛虫”。每当这时,就特别想念家中的暖炕和火炉。
又是一个黄昏,我和阿霞从学校回家,走得浑身发热。突然一阵寒风卷地而起,直扑面门,我打了个哆嗦,前心后背瞬间凉透。阴沉了一天的天色迅速暗下来,肆虐的狂风中夹杂着雪花。我和阿霞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边跑边念着家里的暖。刚到门边,就听见火炉在大风助力下“轰隆隆”燃得正起劲。母亲就坐在炉边,静静地翻动着炉盘上的馍片,那是给我准备的上学干粮,她的脸上跳动着慈祥的橘色火光。一瞬间,我的心也像被母亲的指尖轻轻抚过,漾起暖暖的橙红。
晚上,厚厚的棉布帘捂在门窗上,把冷冽的空气和飘雪的世界隔绝在外。屋内,土炕暖烘烘的,炉火静静地散发着热量。父亲惬意地斜靠在铺着厚实棉褥的炕头,嘴角挂着温和的微笑,悠然地给我们讲故事。那些故事像在他脑海里生了根似的,讲起来滔滔不绝,从不会卡顿。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讲到兴奋处,还会情不自禁地扯着嗓子哼唱几句。坐在炕边织毛衣的母亲,会抬起头愉快地打趣父亲,受了“嘲讽”的父亲笑得更加灿烂。我趴在父亲身旁,津津有味地听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在闪烁跳跃的炉火映照下,思绪飘飞,生出无数奇妙的幻想。父亲故事里的传奇情节、英雄人物,仿佛纷纷冲破书页的束缚,乘风踏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父亲的钦佩,惊叹于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也正是这些故事,悄然在我心底种下了渴望读书的种子,让我对知识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父亲的故事讲完时,哥哥在炉盘上烤的土豆片也熟了。土豆片两面金黄,勾得人直咽口水。太烫了,我两只手颠来倒去地拿着,咬一口便“丝丝”地呼气,却不忘就着母亲腌的酸菜大口吞咽,那滋味,真是香极了!有时候故事的“作料”是炒瓜子,把生瓜子摊在炉盘上,不一会儿,瓜子的焦香混着炭火的暖意便漫了开来,连棉袄的布料都吸了味。可我和哥哥总等不及熟透就开始嗑,等到瓜子真正炒香时,炉盘上早已所剩不多。
现在,我坐在暖气房里,温度恒定得没有波澜,指尖触不到炉火的温热,鼻尖闻不到炭火与烤食的香气。我忽然明白,令我无比眷恋的从来不是过去的寒冷,也不是寒冷中那团跳动的炉火,而是炉火边母亲翻动馍片的身影、是父亲故事里的温情、是儿时岁月里被爱焐热的每一个瞬间。那些美好的日子永远不会重现,它们随着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随着母亲不可抗拒的衰老隐匿在时间的洪流里。但那些日子,像记忆的光盘,早已随着炉火的温度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温暖了往后无数个寒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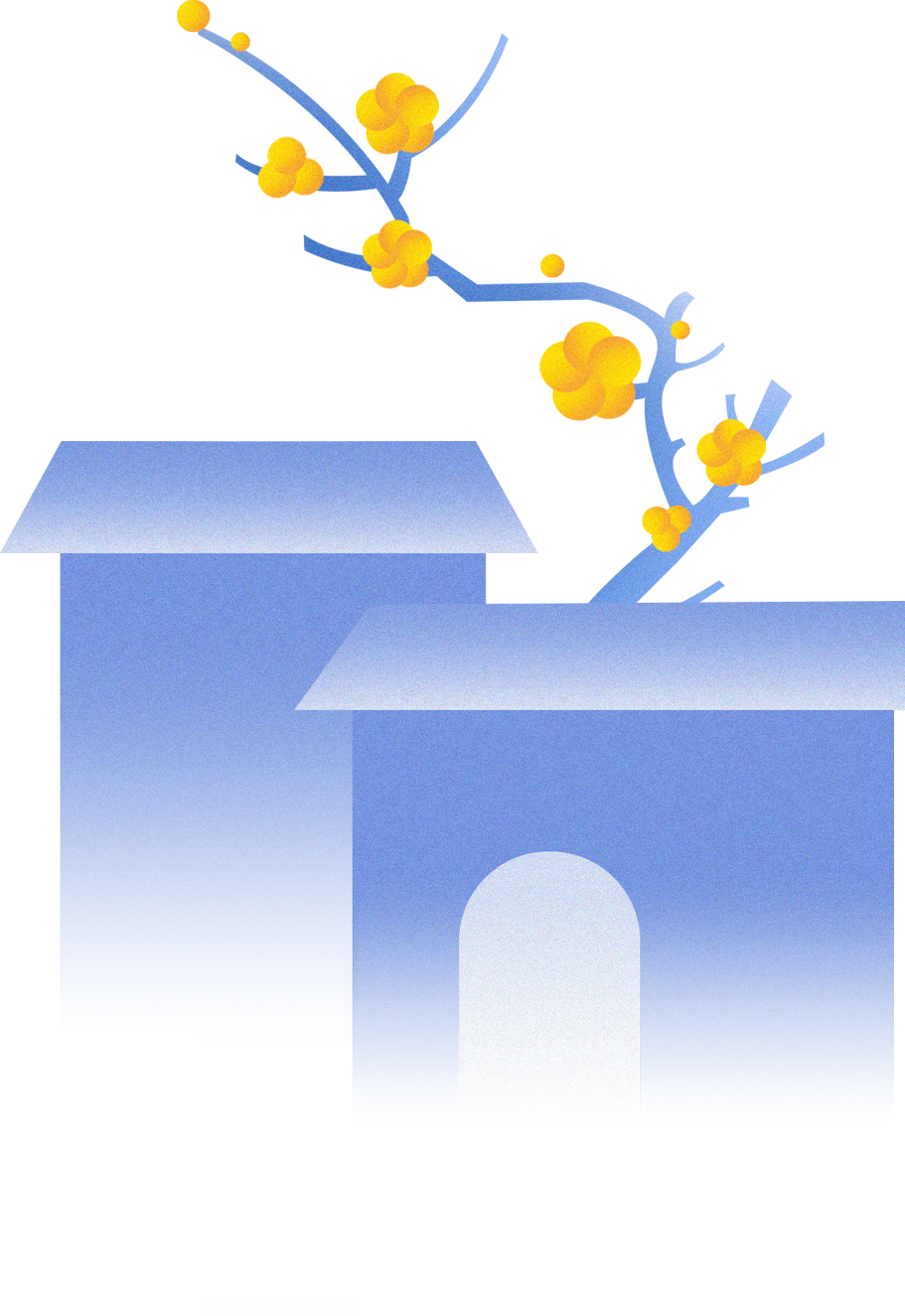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周静
冬日的晨霭尚未散尽,我驱车带着父母,驶向那条通往老家的柏油路。此行是应老家亲戚之邀,回乡吃那心心念念的杀猪菜。车轮碾过熟悉的路径,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时光仿佛在逆流,那些深藏于心底关于杀猪菜的记忆,随之鲜活起来。
老家的杀猪菜,是猪肉、土豆与酸菜在沸腾大锅中的三重奏。猪肉是最重要的食材,取自猪脖子上的刀口肉,也叫脖圈子肉,本地话叫槽头肉。因是农村猪,喂的是野菜和玉米面,其肉质自然纯正、地道。一到冬季,家家户户都要宰猪杀羊,窖藏土豆,腌渍白菜,储备过冬食材。
小雪节气过后的一天,父亲召集村里的壮汉,请来屠宰师傅,要宰杀我家的这头当年猪。一大早,人们陆续来到我家,有一种“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澎湃架势。猪圈里的“二师兄”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机敏与力量。从圈中拖拽它时,它竟挣脱绳索,开始了它的亡命奔逃。那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围追堵截,几个壮汉气喘吁吁,迂回包抄,终于在百米开外的屋角将其合力制服。屠宰师傅是本村的能人,杀猪无数,经验丰富。他沉稳地挽起袖口,口中低吟着古老的偈语:“猪羊一道菜,杀你别见怪,今世还孽债,下世转人来。”话音落、刀光闪,锐利的尖刀精准地刺入猪的脖颈,鲜血顿时如泉涌出,在寒冷的空气中蒸腾起大团白雾。
我早已吓得躲到母亲身后,心怦怦直跳。看着躺倒在地的猪,一股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男人们将猪抬到院子的空地上,烧水褪毛,开膛破肚,分解猪肉。而女人们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李大妈坐在小板凳上,土豆在她手中飞快旋转,不一会儿工夫,盆里堆满了一颗颗白净的土豆。张大婶刀工娴熟,手起刀落,酸菜丝切得匀称细密。母亲则将冒着热气的槽头肉切成厚片,投入锅中。灶膛里,木柴“噼里啪啦”在燃烧。锅里的肉随着火候的升温,发出“呲呲”的响声。随后,放入花椒、大料、酱面儿、葱姜蒜以及切好的土豆、酸菜等,各色食材在沸腾的汤汁中翻滚、交融,浓郁的香气弥漫开来,霸道地钻入每个人的鼻腔,勾引着最原始的食欲。
我像只馋嘴的小猫,早已守候在锅边。等菜烩好了,母亲先笑着盛出一碗递到我手中。我便迫不及待地吹着热气送入口中——肉质丰腴鲜嫩、白菜丝滑酸爽、土豆软糯可口。那是一种直抵灵魂的满足,是童年味蕾上最辉煌的印记。
炕上,父亲和大爷大叔们盘腿围坐,斟上烈性的二锅头,推杯换盏,喝得痛快。酒过三巡,划拳行令声起:“哥俩好呀,三星照呀,四喜财呀,五魁首呀……”高低快慢,顿挫抑扬。有不服输的,撸起袖子再战。有气势如虹的,吼声震天。输者爽快仰头,一饮而尽,赢者抚掌大笑,志得意满。酒至酣处,便有那嗓子敞亮的,即兴吼起粗犷率真的土默川山曲儿:“阳婆婆上来好晒人,娶不过个老婆好爱人”“大摇大摆大路上来,你把你那小白脸脸调呀么调过来”……划拳声、笑语声、灶间的风箱声交织,汇成一曲充满生命力的乡村交响曲。热气腾腾的杀猪菜端上桌来,在那氤氲的香气里,一年的辛苦劳碌都融化在了这喧腾的欢乐之中……
我的思绪被亲戚热情的招呼声拉了回来,眼前的杀猪菜依旧冒着熟悉的热气,吃起来味道依旧纯正、鲜美。可是总感觉少了点儿什么,少了点儿什么呢?也许是那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抑或是那沉淀在岁月深处的、化不开的浓浓乡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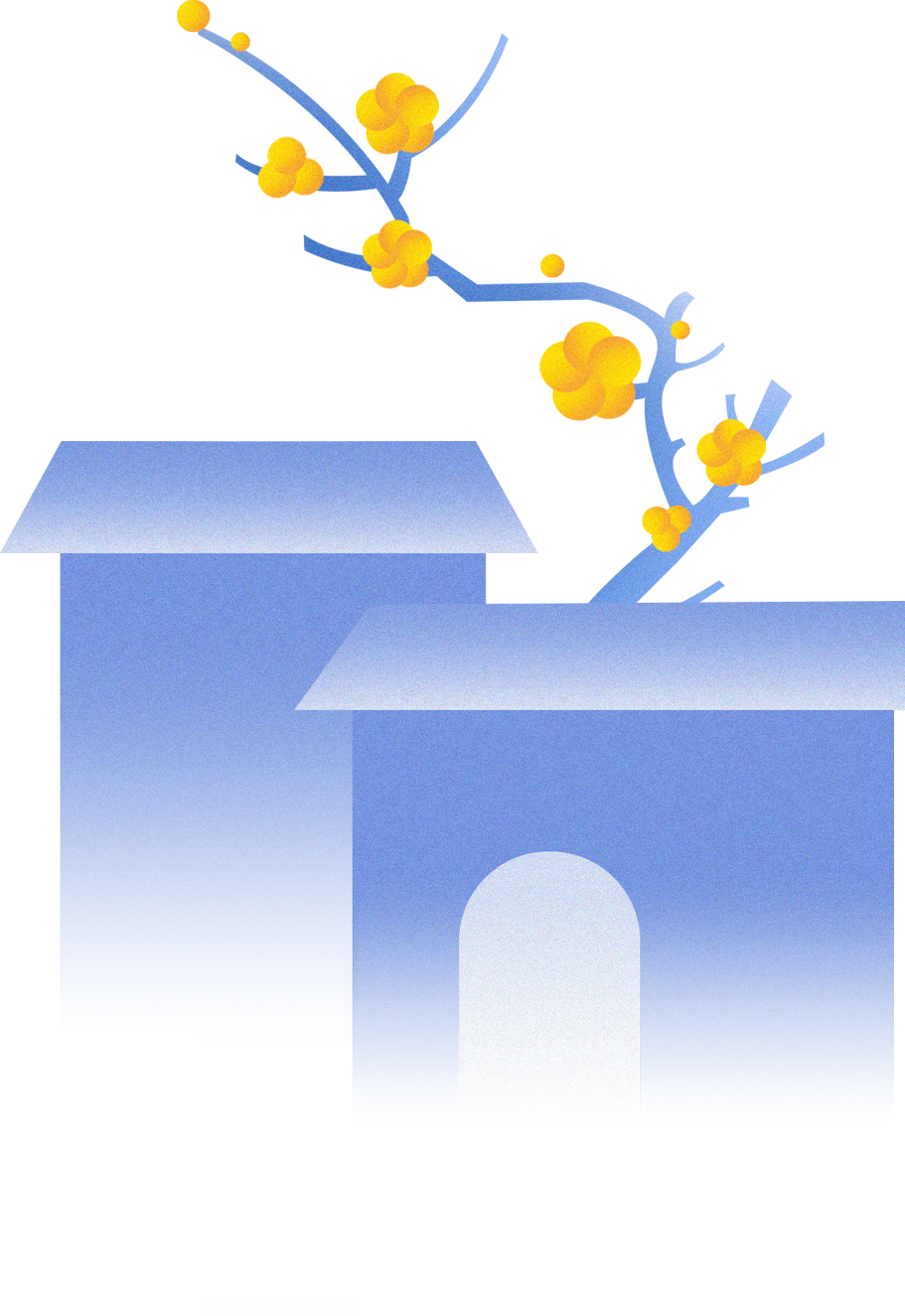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刘东华
20世纪90年代的北方乡村,立冬前,家家户户都要囤秋菜,院子角落的菜窖,是每个家庭过冬的“宝藏地”,窖藏的不仅是萝卜、土豆,更是一整个冬天的温暖与期盼,是刻在一代人记忆里的烟火时光。
姥姥家的菜窖是黄土夯的。窖口不大,刚好够一个成年人弯腰进出,学木匠的大舅用厚实的松木板做了个盖子,边缘钉上铁皮包边,既耐用又能挡严缝隙。
囤菜的日子总是全家出动。姥姥提前把地里收回来的土豆、萝卜挑拣干净,剔除破损的、带虫眼的,只留下饱满结实的。土豆要放在阳光下晒上两天,蒸发掉表面的潮气,这样更耐储存;萝卜则要带着一点儿泥土,姥姥说这样能存住水分,不会轻易糠心。姥爷扛着竹筐下窖,姥姥在地面传递,舅舅们就在一旁帮忙分拣,大家心里满是踏实感——这个冬天,再也不用担心缺菜吃了。有时姥姥还会在窖角铺一层干草,放上几棵大白菜和几捆大葱,青的叶、白的帮,在幽暗的窖里透着生机。
对我来说,下菜窖拿菜,是冬日里最具仪式感的探险。姥爷放下木梯,我会立刻顺着往下走,光线骤然变暗,周身被一股温润的凉意包裹,像是钻进了大地的怀抱。刚下去时眼睛要适应好一会儿,借着窖口透进来的微光,才能看清角落里的“宝藏”。我蹲在土豆堆前摸索,冰凉坚实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专门挑那些圆滚滚、芽眼浅的,仿佛在挑选稀世珍宝,挑够了就放进随身带的小篮子里,让姥姥把篮子拽上去,我则一会儿摸索着数土豆,一会儿闻萝卜的清香,有时还会对着黄土壁小声说话,听着微弱的回声。姥姥总说窖里不能待太久,寒气会渗进骨头里,可我总舍不得上来,直到姥姥喊“我要盖窖盖了”,我才赶紧顺着梯子往上爬。爬出菜窖的那一刻,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脸蛋冻得红扑扑的。
一场大雪过后,院子里的菜窖被积雪覆盖。屋里却暖意盎然,炉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姥姥会挑几个大小均匀的土豆,直接埋进炉膛下的热灰里,借着柴火的余温慢慢烘烤。我们围在炉子旁,一边听着柴火燃烧的声响,一边时不时地问:“土豆熟了吗?”姥姥总是笑着说,别急,慢工出细活。仿佛在等待一场美好的邂逅。大约半个时辰后,姥姥用铁钳小心翼翼地把土豆夹出来,外皮已经烤得焦黑坚硬,还带着草木的烟火气。轻轻一掰,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噗”声,热气裹挟着醇厚的香气瞬间炸开,金灿灿的沙瓤冒着热气,烫得人在左手右手间不停倒腾,却舍不得放下。
剥掉焦黑的外皮,露出沙糯的心,咬上一小口,绵密香甜,带着阳光和土地的味道,还有柴火的烟火气,从舌尖暖到心底。一家人围坐在炉边,手里捧着烤土豆,说着家常话。姥爷讲着田里的收成、姥姥盘算着过年的年货、我们听舅舅们分享着学校里的趣事,炉火的噼啪声、说笑声、土豆的香气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画面。
那时的冬天,餐桌上没有太多花样,土豆、萝卜、大白菜便是常客,可就是这些朴素的食物,在菜窖的守护和炉火的烘烤下,变成了最鲜美的滋味。菜窖里的每一颗土豆、每一个萝卜,都承载着秋收的辛劳与期盼,蕴含着大地的馈赠与家人的爱意。它们在幽暗的菜窖里静静沉睡,等待着被唤醒,然后化作餐桌上的温暖,滋养着我们的岁月。
如今,生活越来越便利,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冰箱、冰柜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那个曾经承载着冬日希望的菜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有的被填平,有的则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坍塌。可那些与菜窖相关的时光,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姥爷挖窖时宽厚的背影、姥姥囤菜时哼唱的小调、我下窖探险时的紧张与快乐、围炉吃烤土豆时的温暖与欢笑……
窖藏的不仅是蔬菜,更是一段温暖的时光,一种踏实的幸福。在那个物质不算富足的年代,人们用双手劳作储存希望,在冬日里慢慢品尝岁月的馈赠,体会着“家”的温暖与安稳。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没有匮乏的焦虑,只有满满的温馨与怀念。那座藏在院子角落的菜窖,那些窖藏的时光,早已化作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提醒着我们幸福的本质:不过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过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品味着大地的馈赠与生活的本真。

《小 雪》(外一首)
作者 / 李春
荷残已尽
菊花傲霜
在这个渐冷的季节
我看到了你凛然的烈性
所有的灿烂
开始收摊
雪花
如天使般
飘然
我回到了
旧家小院
刺骨的西北风
吹散了一切记忆
堆雪人
打雪仗
已一去不返
顺着你薄薄
轻雪上
留下的脚印
我去寻找
空想中
只能漫画出
你轻盈的身姿
偶尔
还会听到
你遥远的
笑声

《大 雪》
作者 / 李春
沉寂了
好长时间
浪漫如
大片大片的雪花
把天地
渲染
冰梭花
是孩子们的世界
堆雪人
捕鸟
成了杰作
有了雪
才有了白毛风
有了直侵肌肤的
寒流
走进村巷
杀猪宰羊的欢笑
温暖了
每户农家
老妈子的大红棉袄
抖了出来
脖子上的白围巾
羞涩着
寒冬中的晚霞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黄韵;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