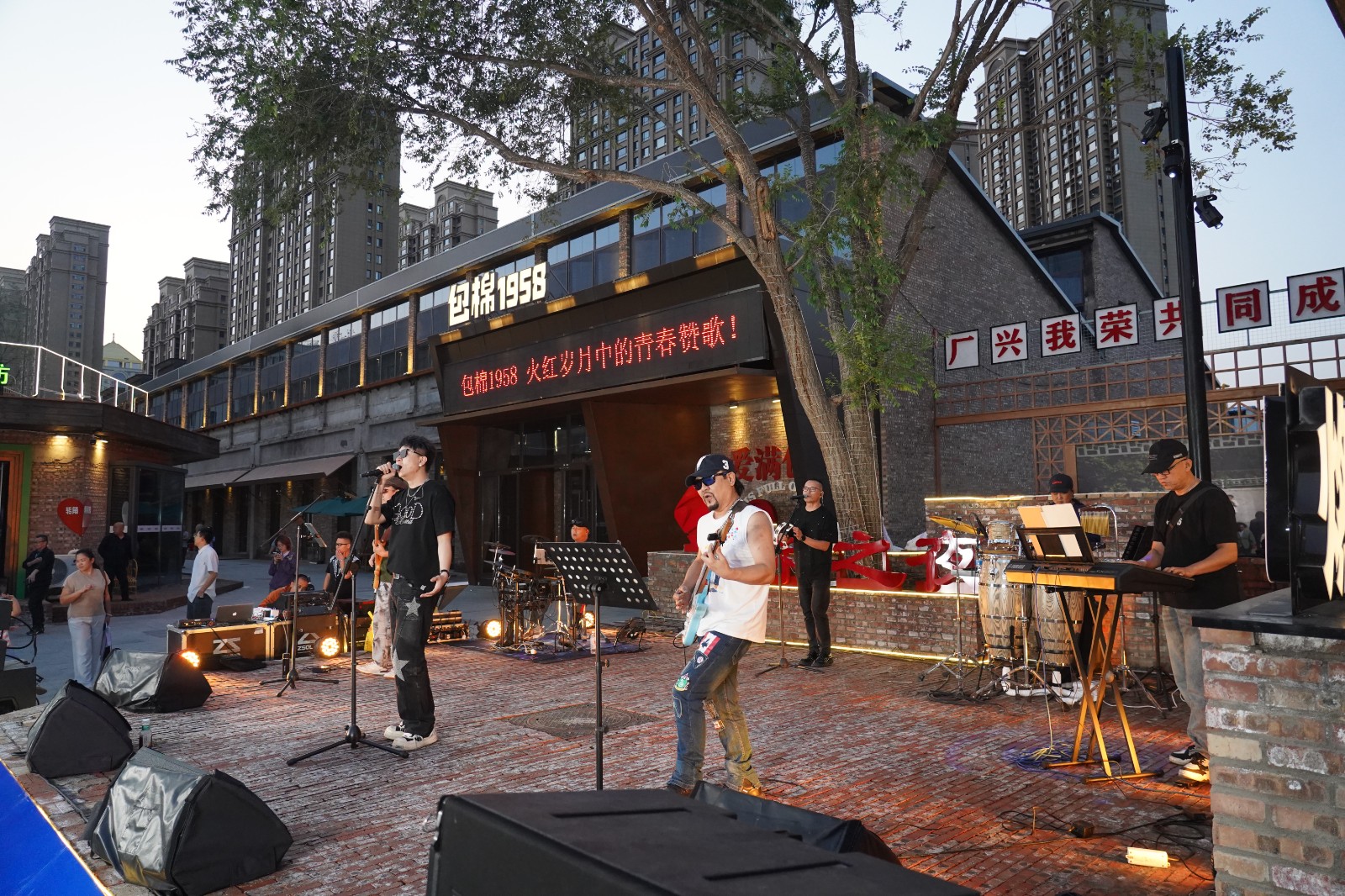伏天里的清凉
作者/刘东华
头伏刚至,热气便迫不及待地弥漫开来,每一丝空气都像是被煮沸过,裹挟着难耐的暑意。这样的时节,记忆不由自主地飘回在姥姥家的暑假,那些质朴却满是温情的消暑时光,如同藏在岁月深处的清凉宝藏,一一浮现。
清晨的暑气还没爬上来,姥姥就已经把堂屋扫得发亮。青砖地用井水擦过,凉丝丝的潮气混着灶间飘来的柴火香,是一天清爽的开端。灶台上,酸粥正在锅里咕嘟着,前一晚泡好的小米在沸水里慢慢舒展,等米粒煮得开花,盛在粗瓷碗里放凉,再加些白糖,味道别提有多香了。酸溜溜的甜混着米香滑进喉咙,一碗下肚,连晨光都变得清润起来。
吃过酸粥,趁着日头还不太高,我们几个表姐弟便戴着南瓜叶或向日葵叶做的“遮阳帽”往村头水渠跑。水刚没过脚踝,清凌凌的能看见石缝里的小鱼,光脚踩进去,凉意顺着脚心往上窜。我们追着蜻蜓踩水,故意把水花溅得满身都是,凉盈盈的感觉特别爽。直到姥姥在渠边喊“该回家吃凉粉咯”,我们才会恋恋不舍地往回跑。
午饭的凉粉是盛夏里的盼头。姥姥的凉粉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知道的是等我们回家时,晶莹透亮的凉粉已经被切成条码在碗里。先撒上翠绿的黄瓜丝、通红的红萝卜丝,再浇上姥姥的秘制料汁和一勺红亮亮的辣椒油,青白红三色在碗里堆得满满当当,看着就让人咽口水。筷子夹起时还颤巍巍的,滑进嘴里,酸辣的汤汁裹着凉粉在舌尖炸开,黄瓜的脆、萝卜的甜混在其中,凉劲顺着喉咙往下钻,刚才在日头下跑出来的热意,瞬间就被压下去了。我吃得急,汤汁溅在下巴上,姥姥总会用手绢替我擦,指尖还带着香菜的香。
午后的太阳像个火球,二舅把大灶旁的鼓风机搬到堂屋中央,插上电,呼呼的风立刻灌满屋子。我们围着风源转圈,衣角被吹得鼓鼓的,大人们坐在板凳上摇蒲扇,话家常的声音混着风声,成了午后最安逸的背景音。

日头偏西时,井台边热闹起来。姥爷把西瓜放进铁桶沉到井里,井壁的青苔湿漉漉的,桶撞在石头上,咚的一声惊起几只蜻蜓。晚饭过后提上来的西瓜,水珠顺着瓜皮往下滴,切开时凉气裹着甜香扑满脸,红瓤里的汁水顺着下巴流,甜得人能眯起眼睛。
临睡前,姥姥总会烧一锅艾草水。青绿色的艾草在滚水里翻腾,满屋飘着清苦的草木香。我坐在大铁盆里,由她用舀子舀着水往身上浇,温热的水滑过皮肤,带着草木的气息,仿佛把一天的燥热都冲跑了。姥姥总说:“这澡洗完,蚊子就不待见咱娃了。”
洗完澡,我兴冲冲地想和表姐们一起在房顶铺凉席睡,便踩着木梯子往上攀,瓦片还带着白日的余温,躺下时却能感觉到夜风顺着房檐溜过来,特别凉爽。没有路灯的光,银河像匹撒了碎钻的蓝丝绒,从东边的树梢铺到西边的房梁上。星星密得像是伸手就能捞一把,忽然就懂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意思——原来诗里的星河,真的会铺在寻常人家的房顶上。可尽管洗了艾草澡,蚊子还是咬得我钻心的痒,无奈,我没躺多久就直跺脚,只好爬下房顶回屋。
刚躺在凉席上,姥姥就拿着蒲扇走过来,见我在挠胳膊,便坐在炕边给我挠痒。她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带着做农活磨出的厚茧,轻轻覆在我的胳膊上,一下下慢慢抚过那些红疙瘩。“用指甲刮才解痒。”我痒得直咧嘴,她却摇摇头:“我的指甲尖,刮破了要发炎的。这样抚抚,气儿顺了就不痒了。”
夜里的热气还没散,姥姥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继续用手抚着我的腿。扇出的风带着她身上的汗味,混着艾草的清香,轻轻飘在我身上。我瞅见她额角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前胸的蓝布衫湿了一大片,可蒲扇摇得稳稳的,抚着我的手也没停。“睡吧,睡着了就不痒了。”她的声音混着扇风的“呼呼”声,像首温柔的催眠曲。
当我半夜热得迷迷糊糊醒来,常看见累了一天的姥姥歪在旁边打盹,手还搭在我腿上,蒲扇掉在炕上。窗外的星光透过窗棂洒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像撒了层碎银。
如今空调房里的冷气很足,却再也没有了那样的夏夜。那些红瓤西瓜的甜、凉粉里的青白红三色、房顶上的星河,都不及姥姥那双手。粗糙的掌心抚过红疙瘩时的温柔,比井水更凉,比星光更暖,把整个盛夏的燥热,都酿成了记忆里最清润的甜。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