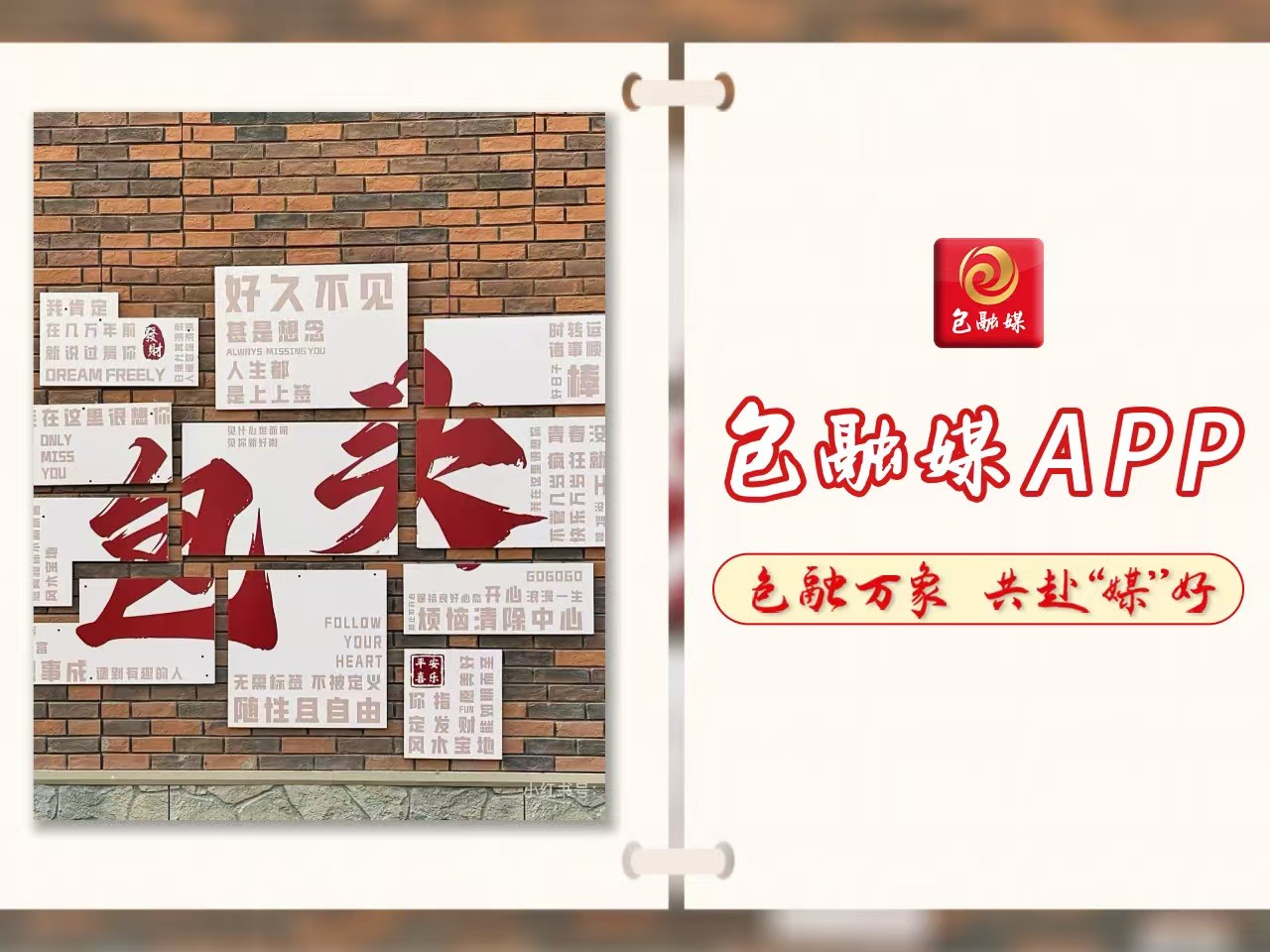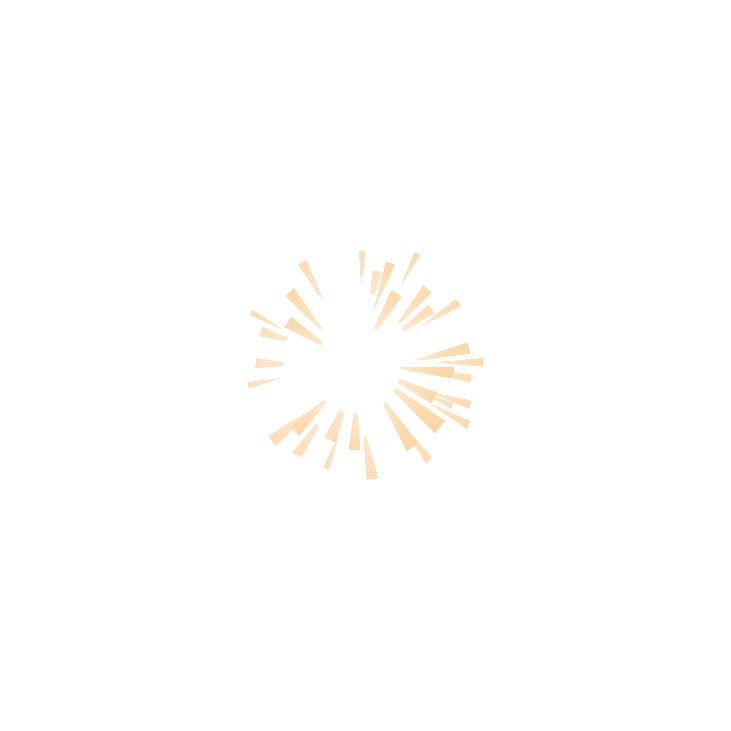
《在沉思的边缘》汇聚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生活、工作以及更广泛社会现象的观察,展现了作者在不同领域和层面的思考。本书不仅是作者个人思想的结晶,也是对读者的一次心灵邀约,邀请大家在生活的喧嚣中寻找宁静,在工作的忙碌中寻找意义,在人生的旅途中寻找方向。

□张伟
从教四十年,对一个人的读书状态能够做出基本的衡估。坐下来和对方聊一聊,或者读他的一两篇文章,大致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在沉思的边缘》,反映出作者在国学方面扎实的功底和深入的思考。作者阅读量之大、阅读面之宽,令人钦佩。而且,不是浏览,是剀切的研读。
傅民同志浸淫于典籍之中,游刃有余,以我注六经的严谨态度,旁征博引,钩沉索隐,无疑是潜心啃过原典的。在这本书里,儒释道,融会贯通;经史子集,互为参证。
有人张口闭口“国学”云云,好像国学是他们家小院里栽种的茄子辣椒,可以随便采摘。谬也。我写文章,慎用、不用“博大精深”这个词,而国学的确是博大精深的,很多人都还没有登堂入室。于是我们看到,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从国学中挑拣一些哲理性的句子装潢、点缀,就自以为是国学通人了。国学被这些人玩坏了,因而常常被污名化。
国学之不易得,至少有三难。其一,文言文的文本,言文分离,有些篇什佶屈聱牙,非有小学、训释之功,是啃不下来的。文言文以单音节词为主,即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粗通文墨者望文生义,以今释古,谬以千里,常常笑话百出。其二,四库之二曰经、曰子,多哲学论著,“形而上者之谓道”,思辨性强,抽象度高,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很难把握其精髓。其三,有些学问,自带神秘色彩,或被后人附会上了神秘的光环。老庄,就是这样。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不知所终,活了五百岁云云,不神秘吗?魏晋时期的哲学,更以玄学相标榜,玄而又玄,这些都是需要祛魅的。
儒道互补,是老话题了。儒家主建构(“文之以礼乐”“修饰之”“润色之”),道家主解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儒家讲入世(“兴废继绝,润色鸿业”),道家讲出世(“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儒家推崇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标举无为(“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有了儒和道这两种矛盾着又补充着、增益着的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才好安身立命,进有进路,退有退路,找到心理上的制衡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的心理平衡了,这个世界才会是和谐的。人的心理倾斜了,世界也必然颠三倒四。因为,我们总是通过心理这面镜子看世界的。佛教传入,中国化而成禅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佛教本来是让人弃绝家庭的,到了我们这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居然有了送子观音。宋明两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儒为宗,融入道、释,三教合流,推动着中国思想的发展,形成开阔而肥沃的三角洲。作者克服了一些人把某种思想定于一尊的偏狭,兼收并蓄,转益多师,而又能鉴别良莠,去伪存真,刮垢磨光,发掘之,弘扬之。
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古代老百姓通过观赏戏曲接受哲人的思想,从而谙熟为人处世之道。《边缘》一书也多处以生动可感的戏曲作品来诠释抽象的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血肉丰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针对厚经薄史指出,六经皆史。经与史互证,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边缘》一书正是这样的路径,翔实而确凿的史料,与立论相得益彰。作者对宋型文化的推崇,就表达了很有价值的观点。有时参之以西方文明,在异质的坐标系里,看得更分明,如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命题。这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开阔视野。新闻人出身,仍然葆有这种职业敏感,古今勾连,用事实说话,以当下发生的典型事件相佐证。
书名里的“边缘”,显然是作者的自谦,非边缘也,乃正道也,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高扬价值理性,守正而能创新。正如代序标题所示,良知、敬畏,是这本书可以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构成了这本书的纲领,在我看来,这也是切中当下症候的要害所在。作者思维的触角伸展得很广远,在“第二个结合”上致思,聚焦于文明的大课题。六经注我,我想改一个字,六经烛我,这个“我”,可扩延为广义的今人,用先贤的思想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作者没有泥古不化,而是取学以致用的精神,正本清源,而后开出思想处方。
概念常常成对出现,《周易》就拈出阴阳这一对核心范畴。我理解,辩证法在成为方法论之前,对立面的统一,它首先是客观事物的本来样态,哲人以其智慧揭橥了世界的奥妙,如此而已。我们看到,《边缘》在相对待范畴之间展开思考,灵与肉、精神与物质、文化与文明、有用与无用、知止与进取、富与贵、有意义与有意思,等等,“既要……又要……”的句式,也成为一种表征。
当下的文化生态,浅阅读是个痛点。如果说,一介平民的浅阅读,束缚了他个人的认知阈限,那么,领导干部的浅阅读,就会对决策、理政带来负面影响。应邀到各单位举办讲座,发现会议室主席台上的会标都是一样的,中间偏上有“道德讲堂”四个字,敦敦实实的,电脑里有的字体,我说不出是什么体。左下角是老子像,右下角是雷锋头像,戴皮帽子那幅。第一次见到,没多想。后来去其他单位讲课,看见如出一辙,不,本出一辙,原来是有关部门统一设计,要求各单位如法炮制的。雷锋的头像出现在道德讲堂的会标上不难理解,他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是精神上永不落山的太阳。老子像怎么也成了道德讲堂会标的设计元素呢?我想了想,大概因为老子的五千言著作叫《道德经》吧。然而,殊不知,此道德非彼道德也。古汉语里,单音节的词为主,“道”是一个词,“德”是一个词。《道德经》里,“道”字出现73次,“德”字出现45次。何谓道?大家都熟悉一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省去中间的数字,可缩略成“道生万物”,意即道是世界的本源,引申为事物的规律。何谓德?“德”是个通假字,也就是古人写的错别字。今人写错别字不能原谅,古人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字不够用,就借用了,一字多义极其普遍。就像单位人手少,一个人负担好几摊工作,是一个道理。“德”与“得”通假,是“得到”的意思,在这里,可意译为“掌握”。因此,《道德经》书名中的“道德”可以解释为:世界的本源、事物的规律,以及人对规律的掌握。可见,它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伦理道德”中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伦理学里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该文集还收录了作者十余年前的几篇随笔文章,如《谁是贵族》。该文是有感于当下只追求物质之“富”而忽视精神之“贵”,造成一些人头脑中的意识混乱而生发的感想。作者引用《随笔》杂志一篇题为《现今中国只有富没有贵》中的一段话“贵族的内涵是学识、是教养、是道德、是尊严、是文明、是理性、是仁慈、是情义,是世代门风培育出来的做人品格”,来厘清当下、尤其是年轻人对所谓“贵族”的认识误区。在论及过往的贵族“骑士风度”时说“这实际是一种发自内心、骨子里的东西:彬彬有礼、慷慨仁慈、勇敢正直,为信仰甘愿奉献生命和青春”。文章还说到“孔子、司马迁、李白、岳飞、杨家将、文天祥正是以其对信仰和尊严的抵命保卫、对炙热家国情怀的忠贞护佑,才成就了中华民族最可期许的高贵血脉承续”。这些文字表达,也与作者始终推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气节”一以贯之。
浅阅读,就我所接触的一些干部,大都没能逃过此劫,信息渠道单一,读物浅显以至错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而无暇阅读,阅读量小得可怜,使得他们的思维搁浅在沙滩上了,难免跌落成指鹿为马的笑料。这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了,而关乎地区事业的发展。想必作者痛感于此,用了一连串的短语,“快餐式传递、浅薄式演绎、功利式表达、流量式吸睛”,笔伐之,针砭之。建议有关部门,以《在沉思的边缘》的出版为契机,在干部中倡扬学习的风气,让阅读充实内心,资政益智,进而提升干部的理政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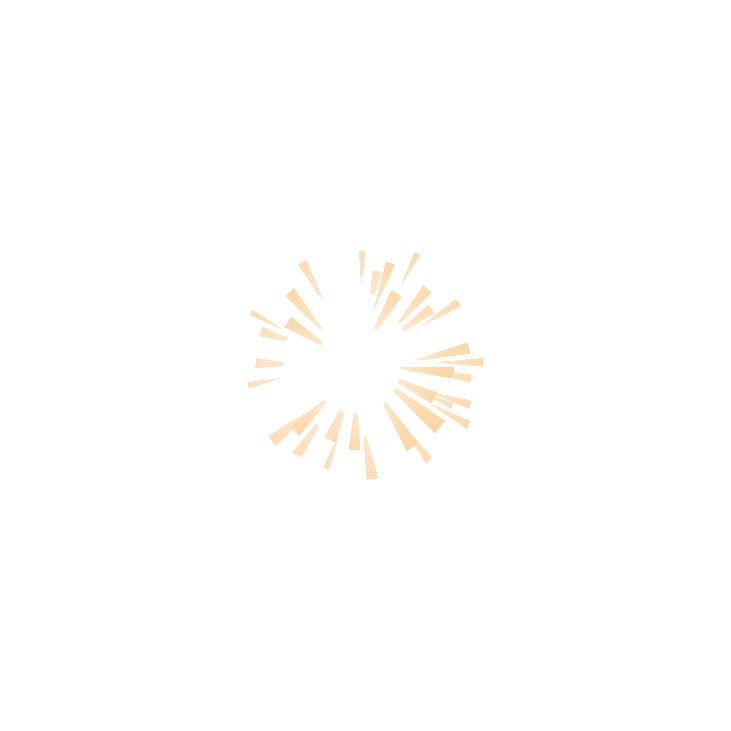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收录14篇历史特写,聚焦拜占庭陷落、滑铁卢之战、南极探险等决定人类命运的瞬间。书中展现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的碰撞,如拿破仑因格鲁希的犹豫而败北,列宁乘封闭列车点燃革命。茨威格以戏剧化笔触刻画英雄与失败者,揭示历史转折中的偶然与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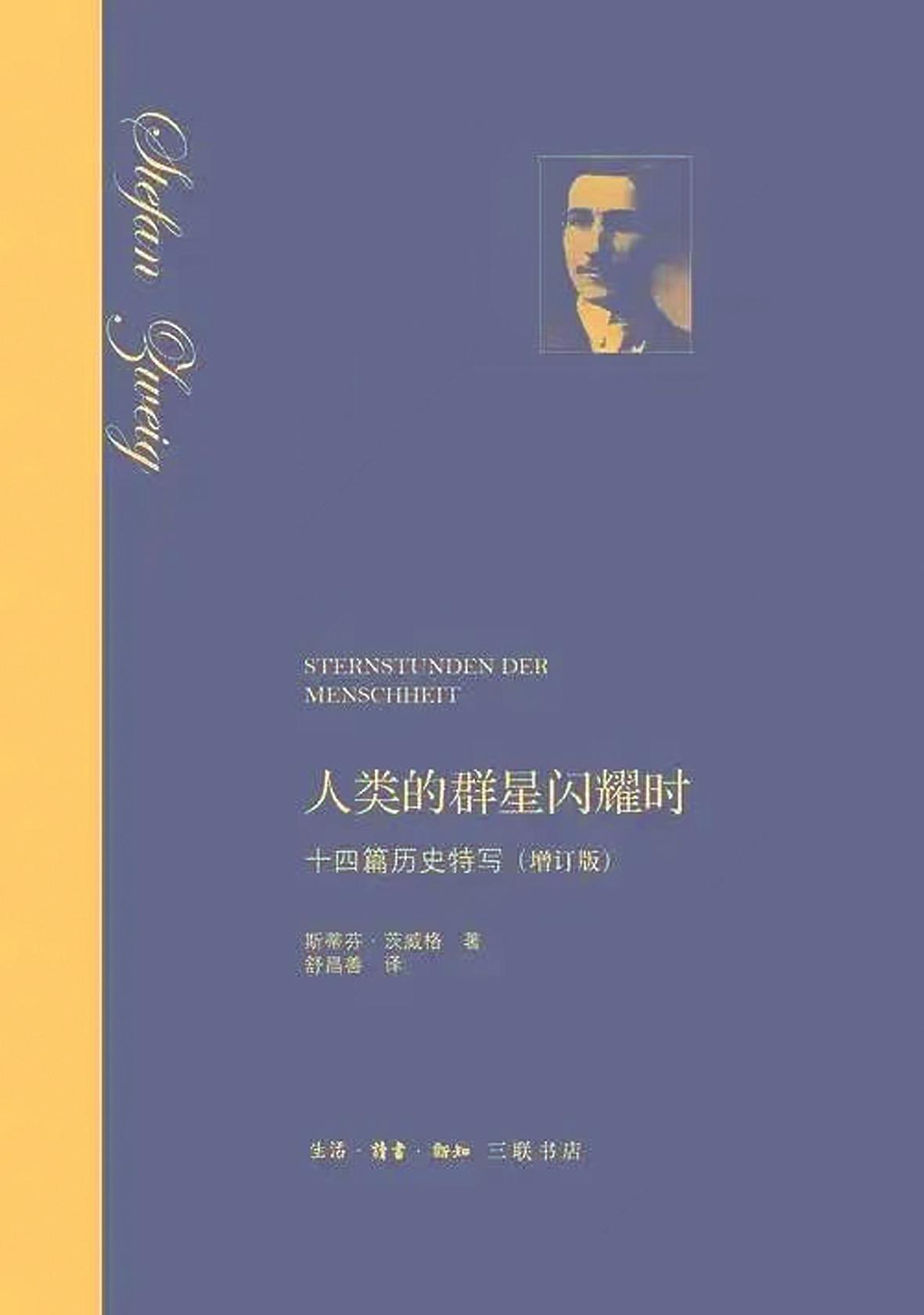
□梁学东
在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著作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它。”这句话揭示了茨威格历史观的核心——历史本身具有戏剧性和诗性,那些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瞬间往往充满偶然与意外。
当我们捧起《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跟随茨威格的笔触,一种激动、追问的心流悸动不已。从太平洋的发现到南极探险的悲壮,从《马赛曲》的诞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救赎,一个深刻的悖论逐渐显现:那些被我们奉为“英雄”、“天才”或“伟人”的历史主角们,在决定性时刻来临时,往往并不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准备或优势。他们之所以成为“群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恰好站在了历史光束照射的位置。这种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构成了对传统英雄史观的一次温柔解构。
茨威格在书中选择的十四个历史瞬间有一个共同特点:主角们几乎都是被命运推上历史前台的普通人。不妨看看这些人物:太平洋的发现者巴尔沃亚是一个为逃避债务而躲进木桶的亡命之徒;创作《马赛曲》的鲁热只是个业余音乐爱好者,此后再无杰出作品;决定滑铁卢战役命运的格鲁希元帅是个平庸的指挥官;甚至文学巨匠歌德,在写下《玛丽恩巴德悲歌》时,也只是一个为少女爱情而痛苦的七旬老人。茨威格刻意避开了那些准备充分、理所当然的历史时刻,而是聚焦于各种阴差阳错、歪打正着的转折点。这种选材本身就在暗示: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存在于计划之外,英雄与凡人之间的界限比我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
在《逃向苍天》一章中,列夫·托尔斯泰的死亡被描述得极具象征意义。这位文学巨匠晚年离家出走,并非出于某种崇高的预先规划,而是在家庭矛盾与内心挣扎中的仓皇逃离。茨威格写道:“这位83岁的老人像小偷一样在黎明时分溜出自己的房子。”这个形象与人们心目中伟岸的文豪形象相去甚远,却更接近人性的真实。托尔斯泰的死亡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但这种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后人赋予的,而非他本人精心设计。同样,《南极探险的斗争》中的斯科特队长,他的失败比许多成功更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的心灵。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意义与个人意图之间常常存在巨大鸿沟,正是这种鸿沟体现了历史的讽刺与深刻。
格鲁希元帅在滑铁卢战役中的犹豫不决,成为茨威格笔下“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的典型案例。拿破仑的命运,乃至整个欧洲的格局,悬于一个平庸将领的一念之间。茨威格以小说家的笔法重现了那一刻:“格鲁希思考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这一秒钟的思考没有任何非凡之处,格鲁希只是按照常规军事逻辑做出了保守决定。然而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普通选择,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被无限放大。茨威格似乎在问:如果那一刻格鲁希突然灵感迸发,或者传令兵早几分钟发现普鲁士军队,欧洲历史会不会完全不同?这种对微小偶然的强调,放大了偶发因素的独特作用。
在《黄金国的发现》一章中,瑞士移民苏特尔发现加州金矿的故事尤为耐人寻味。这个原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终却在财富带来的混乱中失去了一切,沦为乞丐。苏特尔的故事揭示了历史进程中意图与结果的荒诞背离——他发现金矿本是为创造财富,却引发了淘金热,导致自己的庄园被侵占,家庭破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法律诉讼虽然获胜,却无法执行,因为新成立的加州政府无力对抗淘金者形成的“自然力量”。苏特尔个人的悲剧成就了旧金山乃至加州的繁荣,这种个体与历史洪流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构成了历史最残酷也最深刻的悖论。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最为感人的篇章之一,《封闭的列车》,描写列宁从瑞士经德国返回俄国的历史性旅程。茨威格生动刻画了这一事件的偶然性:德国为削弱俄国而允许列宁过境,这一实用主义决策无意中为十月革命创造了条件;历史在这里展现了它的幽默感——德国将军们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战术安排,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世界格局。茨威格写道:“这列封闭的列车就像一发炮弹,射向了彼得格勒,摧毁了一个帝国。”
茨威格的历史叙事具有明显的文学化特征,他笔下的历史时刻充满戏剧张力、心理描写和细节重构。这种写法本身就在启示我们:历史的意义与真相究竟是什么。当读者为《马赛曲》的诞生而心潮澎湃时,茨威格不忘告诉我们,作者鲁热此后碌碌无为,甚至记不清自己那晚创作的具体情况;当读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前的赦免而松一口气时,茨威格揭示这一经历如何永久创伤了作家的心灵。这种处理方式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光环在当时可能无从谈及或黯淡无光,那些“闪耀时刻”在发生的当下,可能混乱、偶然且意义不明。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出版于1927年,彼时茨威格尚未经历纳粹上台、流亡巴西和最终自杀的人生最后阶段。但书中流露出他的历史非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或许源于他对一战前后欧洲文明崩溃的观察。茨威格自己既不相信历史进步论,也不认同英雄创造历史的简单叙事,他更倾向于将历史视为一种复杂混沌系统,其中微小偶然可能引发巨大后果。他的这种视角既保留了人的能动性,又否定了简单的英雄崇拜,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维度。
在当今这个强调个人能力与自我实现的时代,茨威格的启示尤为珍贵:我们既不必因自觉平凡而放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也不应盲目崇拜那些被历史选中的“明星”。历史的戏剧性恰恰在于,下一个转折点可能就在某个普通人的普通决定中酝酿。正如茨威格所言:“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在这些时刻到来时,我们或许无法预知自己的选择将被历史定义为何种模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保持人性的敏感与勇气,始终是对抗历史混沌的最好方式。 那些被命运选中的凡人,既是普罗大众的缩影,也是人性光辉的见证——在永恒的天幕下,每颗星辰都曾是凡人,而每个凡人都可能成为星辰。
在茨威格看来,历史没有剧本,那些最耀眼的星辰,也不过是恰好被历史探照灯捕捉到的凡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既能对历史保持敬畏,又能对自身潜力怀抱希望——在适当的光线条件下,任何人的轮廓都可能被投射成历史的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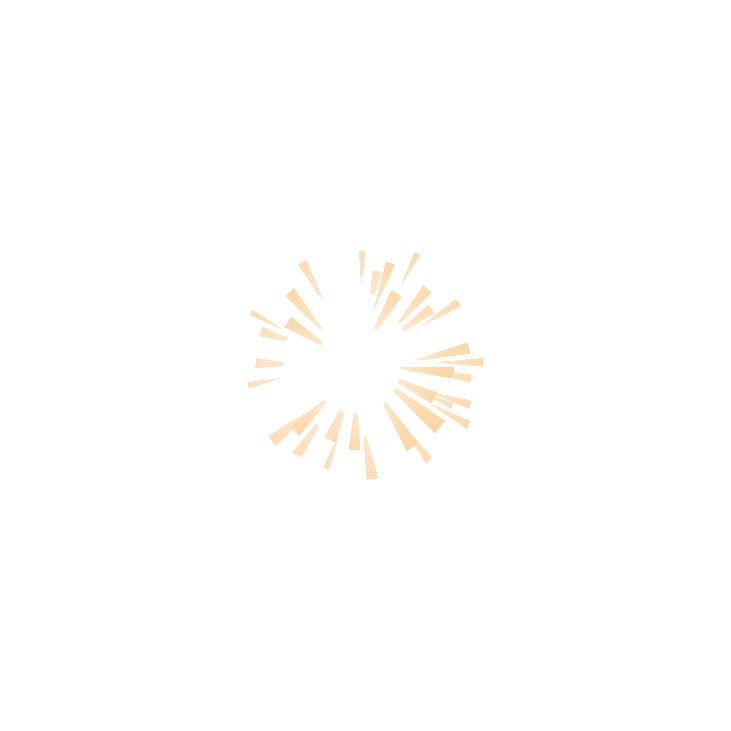
《昆仑约定》是毕淑敏202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为背景,讲述女卫生兵郭换金等战士在极端环境中坚守国界、淬炼生命的故事。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刻画戍边战士的家国情怀与人性光辉,展现理想主义与残酷现实的碰撞。全书近70万字,被誉为“高原军人的生命史诗”。

□李春燕
合上书页时,窗台上的绿萝正舒展着新叶,阳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下暖融融的光斑。这寻常的午后,却因《昆仑约定》里的昆仑雪山,变得格外不同——那些在海拔五千米的冰原上挣扎、坚守、绽放的生命,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里,被忽略的重量与温度,也让我们对生活本身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们总在抱怨生活轻飘飘的,抓不住重心。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我们早已不必为生存殚精竭虑,却在安稳中丢失了生活的锚点。可昆仑山上的人从不用纠结“意义”二字——当呼吸都需要拼尽全力,当一场风雪就可能改写命运,活着本身就成了最坚硬的支柱。他们为战友缝好伤口时专注的眼神,为牧民接生时绷紧的神经,在界碑前站成雕塑时挺直的脊梁,这些具体的事像坚韧的绳子,把零散的日子串成了有重量的生命。反观自己,常常在“今天要不要点外卖”“周末去哪里玩”的琐碎里打转,不是日子太浅,是我们没给它装上“承重梁”。就像邻居张阿姨,退休后总说“日子空落落的”,直到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每天帮老人买菜、给孩子辅导功课,脸上的笑容才重新有了光彩。或许生活的意义从不在远方的宏大叙事里,而在“把这杯热水递给生病的同事”“把这篇稿子改到满意”的具体里,像昆仑的战士们那样,让每一个动作都扎根在真实的需求里,日子自然就稳了。
从生活的重心转向生命的韧性,书中的苦难也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我们总在刻意回避苦难,将其视作不幸的标签,仿佛提及便是对生活的辜负。可《昆仑约定》里的苦难从来不是用来卖惨的,它更像一块试金石,滤去浮尘,显露本真。麦青青从带着优越感的“镀金者”变成能在雪地里跪救伤员的战士,不是因为苦难有多浪漫,而是苦难扒掉了她身上的虚饰,让她看见自己心底的柔软。这让我想起去年夏天,小区遭遇暴雨内涝,平时总抱怨“人情淡薄”的王大哥,第一个蹚着齐腰深的水帮一楼住户搬家具;那个常说“工作没意思”的同事,在疫情期间主动申请值守单位,连续半个月没回过家。苦难从不是值得炫耀的勋章,它只是帮我们擦掉蒙在心上的灰,让我们看见自己本来就有的温度。原来我们不是冷漠,只是太平顺的日子里,那份善意被藏得太深了,需要一点风雨来唤醒。
当我们读懂了苦难中的善意,便更能体会那些藏在细节里的联结。书中那些没说出口的约定,远比任何誓言都动人。战士们分食一块压缩饼干时交换的眼神,递过暖手宝时沉默的默契,临终前那句轻得像叹息的“拜托了”,这些细碎的瞬间里藏着最结实的联结。我们总在追求“轰轰烈烈的情谊”,却常常忽略母亲电话里那句“不用惦记”背后,悄悄晒好的棉被;忽略朋友吐槽“你真麻烦”时,默默放在桌上的感冒药;忽略同事争执后,趁你不注意塞进抽屉的润喉糖。前阵子我发烧在家,本不想声张,却在傍晚收到楼下阿姨发来的消息:“看见你家灯没亮,给你熬了点粥,放门口了。”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任何安慰都暖人心。这些没说破的默契,才是生活里的承重墙。原来最好的关系从不是天天说“我爱你”,而是像昆仑的雪一样,无声无息,却能覆盖所有角落,把彼此的生命连在一起。
合上书时,夕阳正为绿萝的新叶镀上金边。忽然明白,昆仑的风雪与都市的霓虹,本质上并无不同——生活从来不是用来比较“谁更苦”或“谁更甜”,而是无论在何种境遇里,都能找到值得坚守的目标,看见藏在细节里的善意,珍惜那些不必言说的约定。就像昆仑山上的战士们,他们或许从未想过“伟大”,只是认真地活好每一天,守护好眼前人,却在不经意间,活成了我们心中的光。而这份光,其实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只待我们用心去发现,用力去守护。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