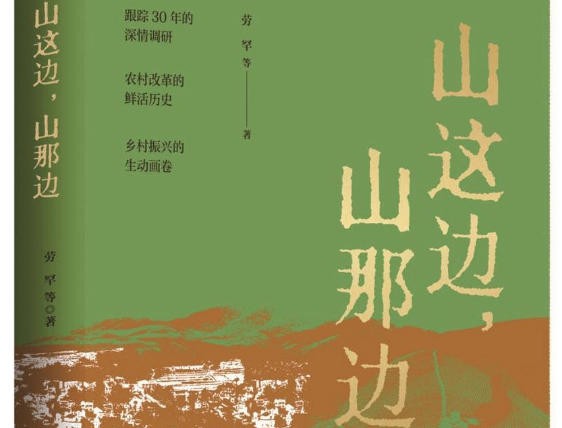烟火气里藏岁月,年味深处是乡愁。
时光的笔触总偏爱描摹那些藏在烟火里的细碎美好,无论是浓情腊月的期盼、灶火油香里的浓浓年意,还是举家迁居、在陌生城市迎接第一个春节的忐忑与欢喜,都是刻在普通人生命里的鲜活记忆。
一箸一蔬里,是寻常日子的踏实;一粥一饭中,是团圆时刻的滚烫;一画一联里,是对来年的郑重期许。这些清苦却温热的过往,皆是人间最珍贵的温柔篇章。
——策划 姬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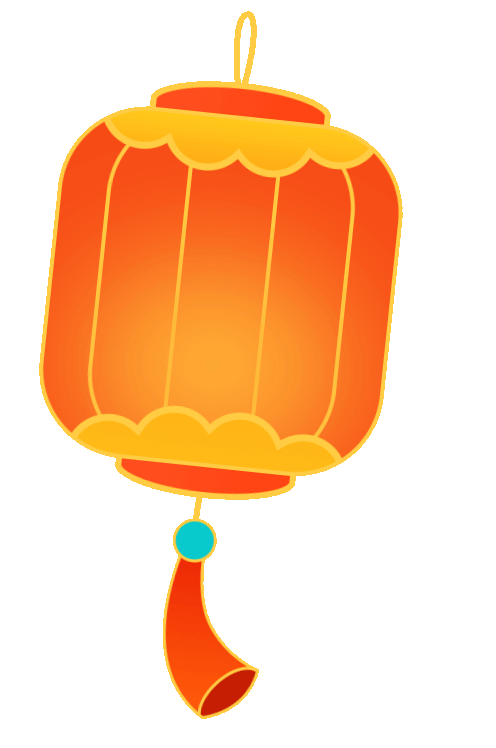

作者/强越珍
脚步匆匆,被日子撵着,又挤进了腊月的门楣。时代变迁,生活富裕的同时,生活节奏却如车轮般疾驰,腊月应有的味道淡了许多,记忆中的腊月裹着烟火浓情,如一束暖光,照亮记忆的长巷……
那些年,腊月一到,年味儿就悄然漫开,家家户户置年货,备年食,炊烟更加缭绕,驱散冬寒,处处透着喜庆,裹着浓情,藏着期许。腾腾热气从门缝里挤出,伴着欢声笑语,柔了时光,暖了岁月。
忙碌是腊月的主旋律。旧时日子清贫,却被勤劳的双手打理得温暖踏实。你瞧,细白的粉条欢腾在大铁锅中,火候到了,母亲盛一碗,浇盐汤、撒葱花、淋上现炝的扎蒙油,简单一拌,滑爽可口;胡麻油滋滋沸腾,香气漫过院墙,橙黄筋道的炸油糕外焦里软,咬一口,绵甜红豆馅儿满溢唇齿;开了花的雪白馒头出锅了,麦香扑鼻,再点上红点儿,满是喜庆。一笼脆麻花、一盘香馓子,一盆鹅黄滚圆的萝卜蛋蛋和肥瘦相间的肉馅蛋蛋;齐刷刷嫩淋淋的豆芽、酸溜溜脆生生的烂腌菜、香喷喷绵顿顿的猪蹄儿、红茹茹油淋淋的红烧肉……大坛小瓮不再饿着肚皮,圆鼓鼓的,打着饱嗝。闲置半年的凉房盛满年味儿,尽是腊月独有的烟火温情。
街头巷尾也喧腾起来。爆米花的嘭然巨响、卖麻糖的悠长吆喝、磨剪戗刀的清亮腔调,不绝于耳。各色小吃、大红对联、烫金福字、吉祥年画、精致窗花摆满街巷。摊主热情招呼,乡邻细心挑拣,好不热闹。
那会儿,手里没几个钱,人心却极易满足。二斤瓜子、一斤花生、几把黑枣、几颗水果糖,再炒两碗自家种的大豆,便是我们盼了一冬的年节零嘴。几张吉祥年画、几副喜庆对联、几张新鲜窗花,便足以让人喜上眉梢。皱巴巴的钞票,藏着一年劳作的收获;大小包裹里,装着一家老小的欣慰;脸上的笑容、脚下的轻步,满是对新年的憧憬。
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家家户户便开始扫尘迎新了。除去屋里屋外的尘垢,丢弃破衣旧物,规整好心情,以全新姿态迎接新岁。
晴好的日子,拆洗被褥。晾衣绳上,花花绿绿的被褥衣物挨挨挤挤,随风轻晃。晾干后,母亲坐在炕头缝补,旧被褥虽失了光鲜,却干净整洁,温暖舒适,裹着洗衣粉的清香与阳光的暖意。
粉刷房屋虽辛苦,却也让人期待。一大早,母亲在火炉上熬煮着白泥,我们兄妹把被褥、炕毡搬到院中晾晒。哥哥粉刷墙面,我和姐姐清洗家什,闲暇时便剪窗花,分工有序,忙而不乱。日头西斜时,昏暗小屋焕然一新,墙面洁白亮堂,屋内一尘不染。窗户换上新麻纸,贴上亲手剪的窗花,咋看都喜欢。屋内炉火正旺,我们接着贴年画:天安门背景下的毛主席笑容慈祥,红鲤鱼驮着胖娃娃充满活力,四扇屏上“龙凤呈祥”“海瑞罢官”“五女拜寿”图文并茂。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年画既装点了年味儿,也悄悄滋养了我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腊月二十九,院落早已清扫干净,物件归置整齐。父、兄张罗着贴对联。父亲捧着对联品读挑选,哥哥站在梯子上比划高低,轻轻抚平边角褶皱。不多时,红彤彤的对联挂满院落,朴素小院瞬间喜气盈盈。
那些年的腊月,雪总是说来就来。雪花飘飘洒洒,覆满小院,装点山川,为烟火人间添了诗意浪漫,也带给人们丰收的希冀。
腊月二十九的夜晚,全家人沉浸在幸福期待里。母亲盘点年货,给我们整理好新衣。晚饭后,羊骨头或猪骨头下锅慢炖,浓郁肉香溢满全屋。我摸着枕边的新衣裳,在诱人香气里,满怀憧憬酣然入梦。
“咣——嘎——”清脆的二踢脚震破清晨的宁静,日子热热闹闹翻到大年三十。换上新衣的小伙伴隔着院墙彼此呼唤着,像小雀儿般欢腾在村庄角落,花花绿绿的新衣裳衬着白里透红的笑脸,纯真又可爱。
晌午,炖到软烂的骨头上桌,油光锃亮、香气扑鼻。一家人撸起袖子大快朵颐,就一口脆嫩的豆芽,酌一口小酒,满足惬意在每个人的脸上。
傍晚,父、兄垒起旺火。“旺火冲天”耀眼在柴堆上,祈盼新年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四更天,一年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到了。震耳的鞭炮声、人们的欢笑声、孩童的嬉闹声,交织成动人的新春交响乐。旺火熊熊燃起,火舌冲天,映红院落,也映红我们的笑脸。“转旺火了!”正三圈,倒三圈,炽热暖意由内而外蔓延,心中涌起无限憧憬。旧年圆满结束,我们以最隆重的姿态喜迎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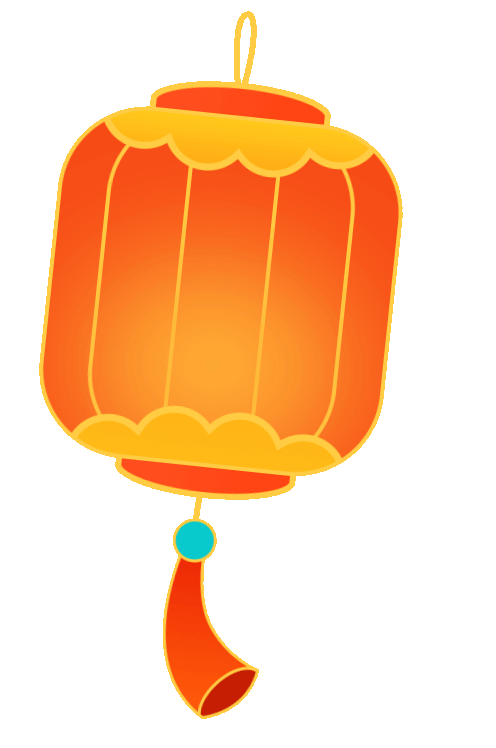

作者/张荣
我照着父亲信中写的详细地址,带着妹妹顺利找到新家的所在时,初冬正午的暖阳好像带了春的气息,和暖地照在我们背上。
新家在城市近郊,和故乡原汁原味的乡村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味道。这里的房屋整齐划一,巷道横平竖直。新房子宽敞明亮,布局合理,更让人兴奋的是,我们要在新家过年。
伯父从他工作的学校借来几张单人床,父亲将其中的两张拼成双人床放在主卧,另外两张拼在客厅给我和妹妹用。母亲将一卷薄薄的印花的确良布剪开做成窗帘,将羊毛毡、棉花褥子铺在嘎吱作响的拼床上。做这些的时候母亲一直严肃着,甚至有些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的嫌疑,我知道母亲的担忧,是农民离开土地的失落,是在这前途未卜的异乡不知如何生存的凄惶。可是,阳光从明亮的大窗外照进来,簇新的粉色窗帘柔和得如一抹霞光,这霞光反射在母亲年轻的容颜上,温暖而和煦,我想安慰母亲一切都会好的,却不知该怎么说出口。
寒冬在几场慌慌张张的冷风里匆匆忙忙地来了。我放学回来,邻家的大爷送来半麻袋卷心菜,倒在冻得生硬的水泥地上,圆滚滚的,白嫩水灵。母亲笑着道谢,却在大爷消失在大门后时收起笑容,呆呆地看着这一地的卷心菜。我说:“妈,一切都会好的,你不是常说树挪死人挪活吗?”
卷心菜是个吃法多样的好蔬菜,可以炖土豆,可以单炒,可以肉炒,可以素炒,还可以凉拌。只是烹饪后的气味有些霸道,那个冬天,新家的每个角落好像都有熟卷心菜的气味儿,伴随着土暖气散发的温热,四处氤氲。夜里,打开的被褥上、隔夜放置的棉衣上,熟卷心菜的气味儿都将我紧紧包围。
清冽的满月的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将一层白霜一样朦胧的光晕染在红躺柜上,炉火渐渐微弱,熟卷心菜的气味儿渐渐淡下去。谈不上多么不喜欢这个气味儿,只是成年后我再未把卷心菜当成蔬菜买过,甚至还牵连了紫甘蓝。
父亲在一个冰冷的黄昏拎回一篮子年货:一小袋奶糖、几斤水果、蔬菜以及肉食,并高兴地对我们说:“看,爸爸买了橘子和苹果,过年吃。”篮子是四姨用铁路货运段淘汰下来的捆木箱的塑料条编织的,一点儿也不大,却装下了我们全家在新家第一个春节的年货。
因另一套房间尚未内部装修,祖父祖母仍留在老家,我们第一次在祖父祖母缺席的状态下过了一个春节。对联是堂弟写的,一大卷,一张张展开,在床铺下压平,大年廿八,我和妹妹端着糨糊跟在父亲后面,欢天喜地,一副副贴上门楣。红艳艳的春联配上崭新的墨绿色门窗,和老家漆皮剥落的褪色门窗相比,必然是要多洋气有多洋气。
母亲看着兴高采烈的我们,脸上也泛起好看的笑容。
除夕夜,父亲在前院两个蔬菜大棚中间的空地上奢侈地用大块的煤炭垒了旺火。在老家,煤炭属于金贵物资,哪舍得这么用,往年的旺火都是烧祖父一整个冬天备好的树枝木棍。入夜,瑞雪初降,我在屋檐下抬头望向天空,白亮的灯光里,大片的雪花簌簌落下,想到年后祖父祖母也会到来,一家团聚即在眼前,心中又泛上无尽喜悦。
母亲依旧在红躺柜上摆了香炉,整个正月的早晨都要点上一支香。她说,在这里过一个年,这就是咱的家了。母亲脸上的严肃与忧心也终于渐渐消失,原来,家庭的氛围全在一位主妇的脸上呀。
春来时,租伯父家闲置房子的南方木匠要转卖一套崭新时髦的组合家具,伯父赶忙替我家低价买进。组合家具搬进来,母亲将红躺柜搬进卧室,原本属于电视柜的地方被它占领,从而也省下一笔买电视柜的钱。
家里来人住不下时,我曾在红躺柜上睡过一晚。干燥平展的柜面,铺了厚厚的棉花褥子,我躺在上面,柜板隐约散发出淡淡的木香,混着隔年樟脑丸的余味,我闻着这从小到大闻惯的气味儿,睡得安稳而踏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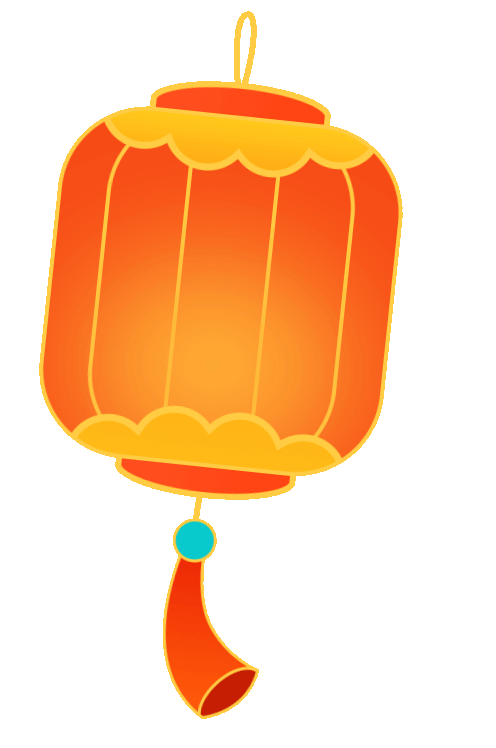

作者/孙少红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写福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把油走,三十晚上闹一宿。”
小时候,北方人家过年,大多是循着这“忙年谣”一步步筹备的。母亲操持着四世同堂十几口人的家事,把日子打理得红红火火,整日脚不沾地、席不暇暖,可再忙,也要让全家人在过年时吃上黏糕。不只是因为黏糕香甜可口,更图一份吉利喜庆——“年”与“黏”同音,“糕”和“高”谐音,寓意新的一年全家人团团圆圆、紧紧“黏”在一起,岁岁平安,步步高升。
腊月二十八,天还未亮,母亲便起身到灶间生火烧水,而后踏着霜花去仓房,从大瓮里盛出黄米面。那是秋日自家田里新收的黏黄米,现磨的新面,带着谷物的清香。
母亲先舀两碗黄米面放入大瓷盆,用滚开的沸水泼面,握着擀面杖朝同一个方向快速搅动,让沸水与黏米面充分交融,直到面稀汤稠、上劲拉丝,直到拉起一米长也不断,便打好了面芡。接着往面芡里分次戗入干黄米面,揉至面团软硬适中,再在面上蒙一层白纱屉布,盆口盖上新高粱秆穿成的盖帘,把面盆端到温热的炕头,裹上厚棉被,让黄米面慢慢醒发、微酵,这个过程要耗费十几乃至二十几个小时。母亲总说,炸糕的面一定要醒发得当,软硬适中才好吃;面太软,炸出的油糕难成型,塌软粘牙、少了嚼劲儿;面太硬,不易发酵,成品口感干硬粗糙。
趁面团发酵的间隙,母亲挑选、淘洗红芸豆,下入大锅煮至软烂,再用豆杵子将豆子捣成细腻黏糯的豆沙,借着豆泥温热软糯的状态,团成乒乓球大小的豆沙馅团。
腊月二十九,天刚蒙蒙亮,母亲又早早起身,在大铁锅里倒入澄黄清亮的黄豆油,点燃灶下的苕条。我蹲在灶膛边帮着烧火,母亲则趁着热油的工夫,把醒发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面团移到面案上揣揉。她常说,油糕好吃的关键,在于不揉面、只“揣面”,把面团揣得光滑筋道,面团不起死筋,炸出来的油糕才松软有嚼劲,放凉也不会发硬。母亲将揣好的面团揪成鸡蛋大小的均匀面剂,双手蘸油,麻利地把面剂按成厚薄均匀的面饼。左手托饼,右手放馅,虎口轻收,将面饼边缘向上收拢,食指与拇指快速捻转,严严实实包好豆沙馅,捏成光滑的圆球,再在掌心轻轻一压,一个胖墩墩、直径七八公分的糕饼坯就成型了。
油面随着火苗轻轻晃动,待锅内油面泛起细密小泡,面案上已摆满了包好的糕坯。母亲拿起糕饼,顺着锅沿轻轻滑入,“滋啦”一声脆响,油锅瞬间腾起油花。母亲拿筷子和漏勺配合着,迅速给油锅里的糕饼一一翻身。素白的糕坯在金黄的油浪里翻旋,渐渐鼓胀,色泽由白转浅黄,再慢慢晕成灿烂的金红,像一朵朵小花绽放在油面上。油香炸开,裹着黄米的香气飘出灶房,飘到院子里,院中的大黄狗都忍不住耸动鼻子,急急地摇着尾巴。二姐和三姐在屋外贴春联,父亲和二哥刚进院门,跺掉鞋上的积雪,把新买的烟花爆竹放进凉房。
屋外北风在电线间吹着尖利的唿哨,屋内灶房里,油锅还在欢唱,一片片油糕被捞起。母亲的脸上映着灶火的光,曾祖父和曾祖母盘腿坐在炕上,端着母亲刚递过来的油糕满脸笑容。我和二哥在灶下,一边往灶膛里添苕条,一边吃着弹牙酥脆的油糕,嬉闹间,鼻尖都沾着油亮。
是母亲的勤劳,让全家人暖和又踏实。

吉祥如意(农民画)折慧刚 作
(责任编辑:吴存德;一审:张飞;二审:刘磊;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