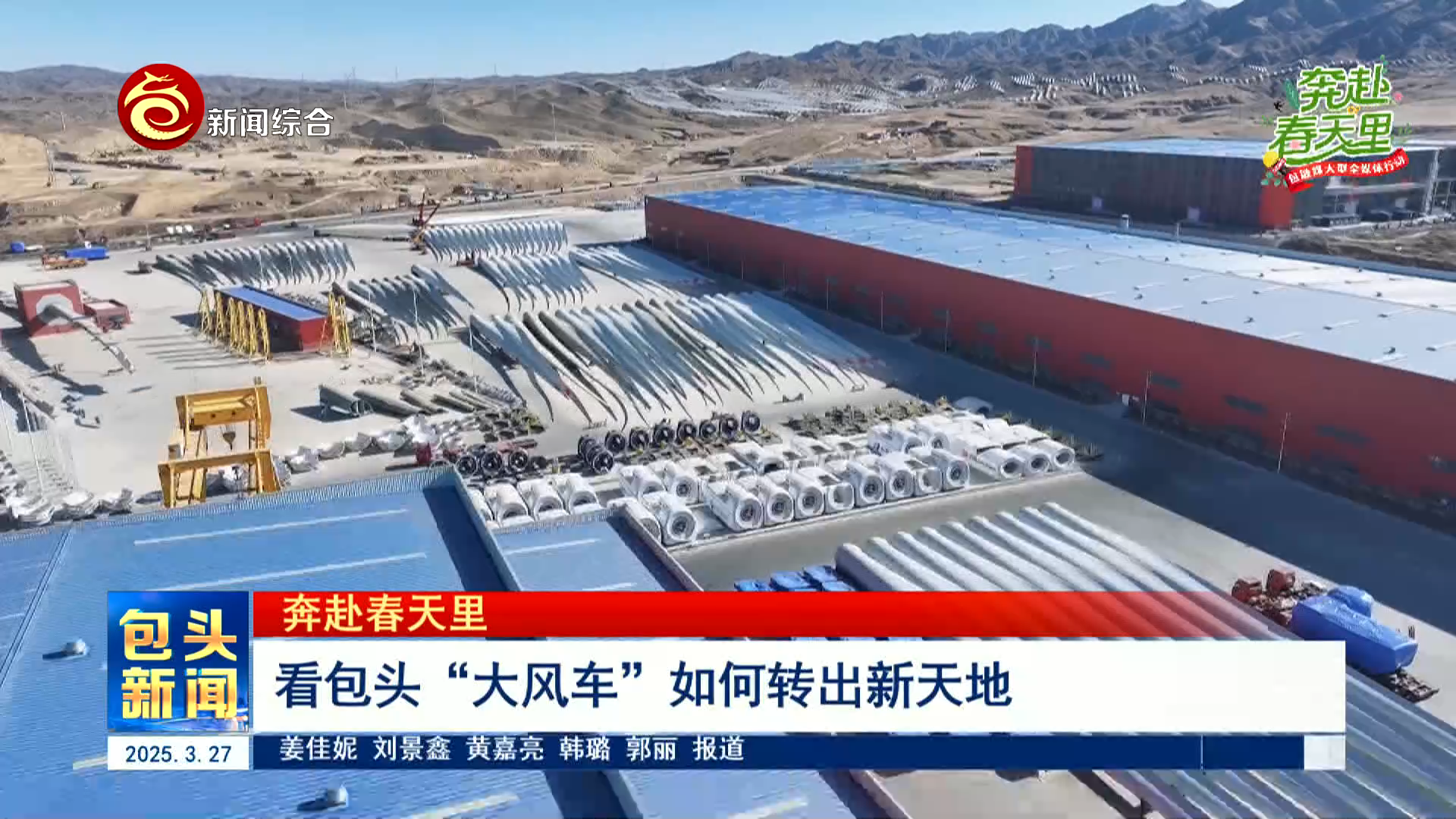□张静娟
两年前的三月,春分刚过,春天的气息渐浓,呼啸的120紧急把母亲拉进了医院。
母亲的昏迷状况,让我一度以为,这一次,她是真的救不回来了。然而,一天一宿地昏迷、挣扎、救治后,八十多岁的母亲竟又神奇地睁开了眼睛,半昏半醒间,对喂进她嘴里的吃喝来者不拒。我们不由得感叹她生命力的顽强和对“活着”的渴望。
这是我们第四次从死神手里抢回母亲。
十二年了,反复地住院、出院。从最初入院时几个人谁都舍不得离开医院,日夜守在母亲身边,精心照顾她吃药打针洗漱吃喝,推着她做各种检查治疗,逐渐到一遇到住院情况,兄弟姐妹几人就开始有序地轮班值守。反复发病住院的持久战日渐耗尽了我们的精力,“久病”也无声地消耗着我们对于母亲的爱。
如果认真回忆,有些镜头依稀还在眼前:
在医院值一宿夜班,早上5点多钟麻烦护士帮我打开心理科住院部上锁的大门,快速在路上买好早点撒腿跑回家,唤起还在上小学的女儿,给她扎好小辫子,安顿好她到点上学后,又迅速冲回医院伺候母亲起床洗漱吃饭吃药……
母亲抑郁症严重到木僵状态,一口水勉强喂进去,却从早到晚僵硬得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更无法交流。我开车回家取东西时,难过、无望地在车里号啕大哭……
人到中年,一边是孩子,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一边是母亲,哪个也放不下,哪边都纠扯。那些年,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
母亲每次住院都情况严重,医嘱从来都是要求24小时必须有人陪护。妹妹和弟弟也一样,他们在单位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为照顾母亲几乎请遍了所有能请的假。
日子突然变得面目全非的时间节点定格在2013年。我始终记得,那一年,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了,73岁的母亲却病了,每天疑神疑鬼地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任凭我们怎么想办法耐心陪伴,怎么竭尽所能地开导都不起作用。春天生发的,有生命,也有逃不开的衰老。时间在这一点上,无论对谁,都公平。
十二年的时光里,母亲从生病初期对我们端到桌上的饭菜挑三拣四的“性情大变”,到最近几年里的日渐失智失能,她知道我们是谁,却不再与我们有任何情感交流。
母亲像是活成了一株植物,静默地站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每天轮流去母亲家端屎倒尿、洗床单拆被褥、做饭,伺候她吃喝、换纸尿裤,日子循环往复,疲惫地迎来一个个日出,送走一个个日落。听闻同事八十八岁的老母亲每天中午做饭等他去吃,甚至还能给他蒸馒头,满满地羡慕。
直到有一天,忽然刷到一个小朋友弹着钢琴唱着一首熟悉的旋律:“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这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
屏幕上,歌词下面备注着“脐带、羊水、妊娠纹、手术灯、未知、医生、手术刀……”这些简单的几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这是一首关于生命、关于母亲的歌。听得我那么感动!之前多少次在不同的视频里听过的这段旋律,从来也没注意过唱的究竟是什么。
我又百度了这段歌词,知道了这首歌的名字是《我记得》。就这样,忽然被一首歌治愈,我又有了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原来,生命的遇见,注定是失忆着相遇;我们注定不记得曾经一起经历过的从前,但是我们注定会因为缘分再次遇见。就像母亲这两年里,偶尔一两次清醒后说“多亏我有这几个儿女”,也是一种治愈。
每天困在母亲的屎尿屁里,有时候真的很崩溃。但人生,何尝不是一种修行。
张静娟,包头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二冶集团职工。散文《流年打马过》获201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征文二等奖。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