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朔风掠过长城,霜雪染白屋檐,北方的冬天便在烟火气中拉开了美食序章。校园夜市的暖光里,年轻的笑语伴着热气蒸腾;茶汤的铜壶边,小米香混着芝麻味漫过街巷;糖炒栗子的焦香缠上指尖;麻糖的甜脆咬开冬日的温柔——这些限定滋味,藏着北方人对抗严寒的智慧,更盛着最踏实的生活暖意。
——策划 姬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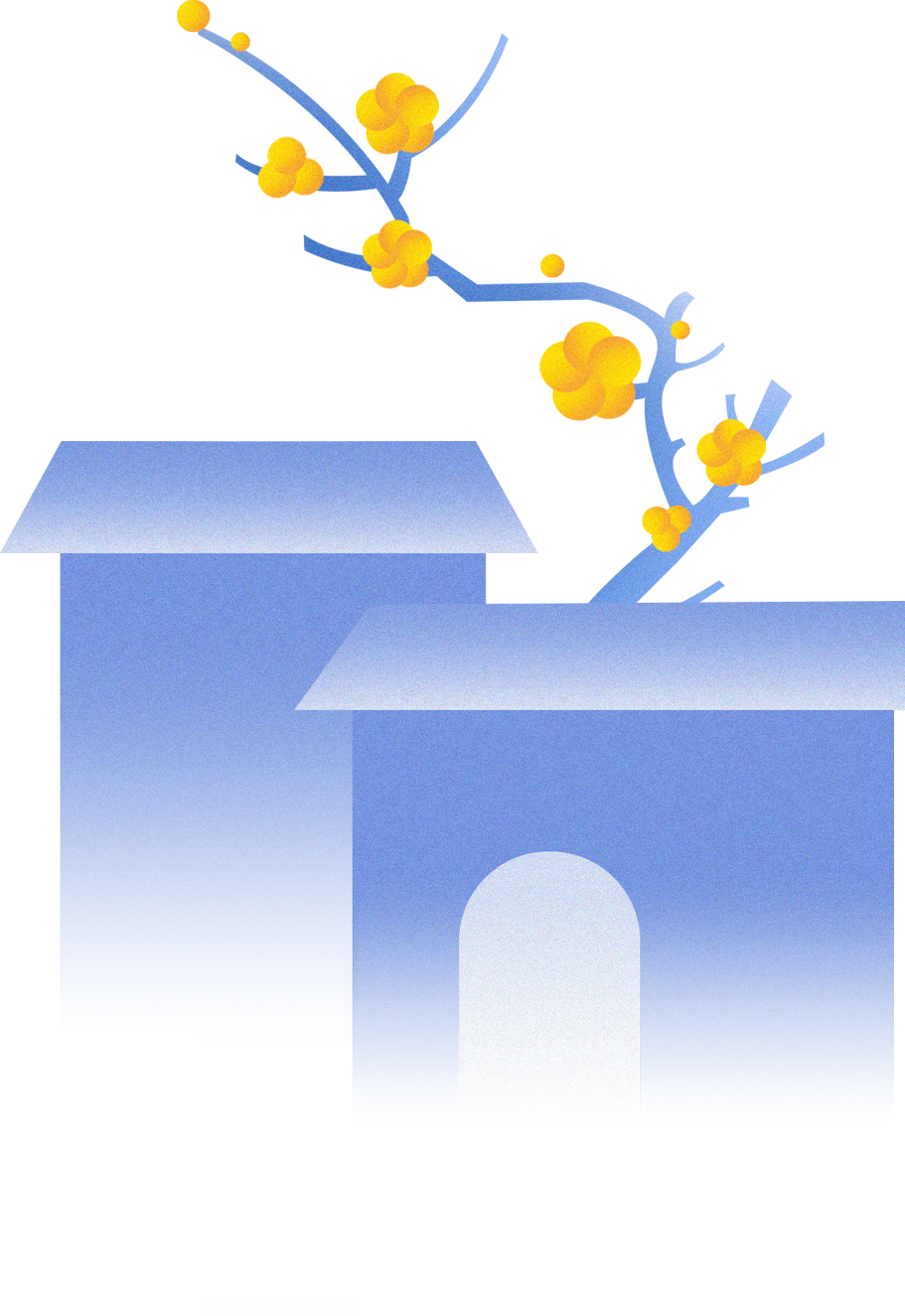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杨月瑗
小时候的我不爱吃饭,任何山珍海味放到眼前均不为所动,“瘦”成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对我最简单粗暴但也最贴切的定义,几乎贯穿我的整个童年。饮食挑剔到近乎要绝食的地步,让全家人都犯了难。可是,无论是小孩中的“人气王”汉堡薯条,还是吱吱冒油的烤串,抑或是裹上麻酱香气四溢的涮肉,都很难打动我的胃。某天,一次无意的讨论,家人们催生出了新的灵感——不妨去尝尝茶汤?
茶汤,作为包头特有的传统小吃,是一种以小米面为主料的甜味米羹,起源于明代,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不同于字面意思,茶汤与茶和汤均无半点关系,如果非说有什么联系,那只能说冲泡的过程类似沏茶。缀有两个红色毛绒球的龙嘴大铜壶是每个茶汤店的必备招牌,庙会上只要看到那泛着古铜色的壶和两点鲜艳的红,便能确定是茶汤的摊位了。只见店家的每个动作都像经过了千锤百炼的仪式,他先舀起一勺小米面,兑水调匀,干粉与凉水须臾间便融合成了少量柔顺的浆体,再将碗放到大铜壶的下方——提壶,弯腰,一道滚烫的水柱便从龙的口中喷涌而出,精准地注入碗中。蒸汽腾起,耳边传来他极为专业的介绍“水要滚,冲要猛,一气呵成,这茶汤才有魂。”水止,面凝,佐以红糖一拌,那便是我人生中吃到的第一碗茶汤。小米的谷物清香在开水的激发下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红糖恰到好处地为略显单调的米糊增添了一抹亮色。只一口,我便爱上了这温暖甜蜜的滋味。
那时候,爷爷还在世,从此每天的固定项目就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吃茶汤。几轮春夏秋冬,习惯从未改变。寒冬腊月,爷爷自己的手冻得通红,却还总让我把手揣到他的口袋中取暖。我常去的那家茶汤店装修极为古典朴素,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小店不大迎东西南北贵客”,下联对着“美食上品保春夏秋冬健康”。进店照例要一碗传统红糖茶汤,我大多时候都会站在铜壶边聚精会神地看茶汤制作的过程,手起水落中一碗喷香的茶汤就能完成。有次老板得意地和我说,要是把碗扣过来,它都不会洒的,说着便将碗翻了个面,我心里一惊,险些要拿手去接,却不承想那茶汤竟真的纹丝不动粘在碗中,对抗着地心引力,实在厉害。
每次爷爷都不吃,只是坐在对面慈爱地看着我,他确信在这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能慰藉他小孙女的魔法。爷爷还总喜欢关切地问我要不要吃糖饼啦,想不想吃麻花啦,或者茶汤里再加点儿什么呢,我每次都只一个劲儿地摇头,他便无奈地笑叹:“你要是能好好吃饭,我比谁都高兴。”
四季就这样在茶汤的热气中更迭,岁月也在爷爷花白的鬓角跳跃。北国的冬天肃杀而漫长,人们都缩进棉衣,动作被寒风吹得略显迟缓,此时,一碗软糯甜香的茶汤总能为严肃的冬日平添一份温和的气质。捧一碗热热的茶汤在手,如同抱住了冬日里的一缕暖阳,随着热气在胃里荡漾开,五脏六腑都会感觉瞬间活了过来,耳朵不冰了,手有了知觉,心里更是充盈着难以言喻的满足。后来店内又推出了好多新口味,台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佐料,有葡萄干、核桃仁、瓜子仁、山楂丁、巧克力和芝麻等,这总让我想起冯骥才在《俗世奇人》中描写的场景:“杨家的茶汤,芝麻要分两次撒,头一层在茶汤将凝未凝时,第二次在将食未食时,为的是香气层次分明。”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仿佛透过书页闻到了茶汤的清香,想起了坐在对面笑盈盈地看着我的爷爷,那是文字永远无法完全承载的独家记忆。
如今那家茶汤店还在,龙嘴大铜壶里的水依旧滚烫,只是我早已不似当年那般瘦弱,爷爷的自行车也早已锈蚀在时光深处,店里熙攘的食客中,再也找不见他的身影。我又一次吃着那碗传统红糖茶汤,舌尖是熟悉的甜糯,眼前浮现出童年的片段——那个小女孩坐在爷爷的自行车后座上,进入每个有茶汤相伴的四季,被爱包裹着。原来,我贪恋的,从来不只是这一碗茶汤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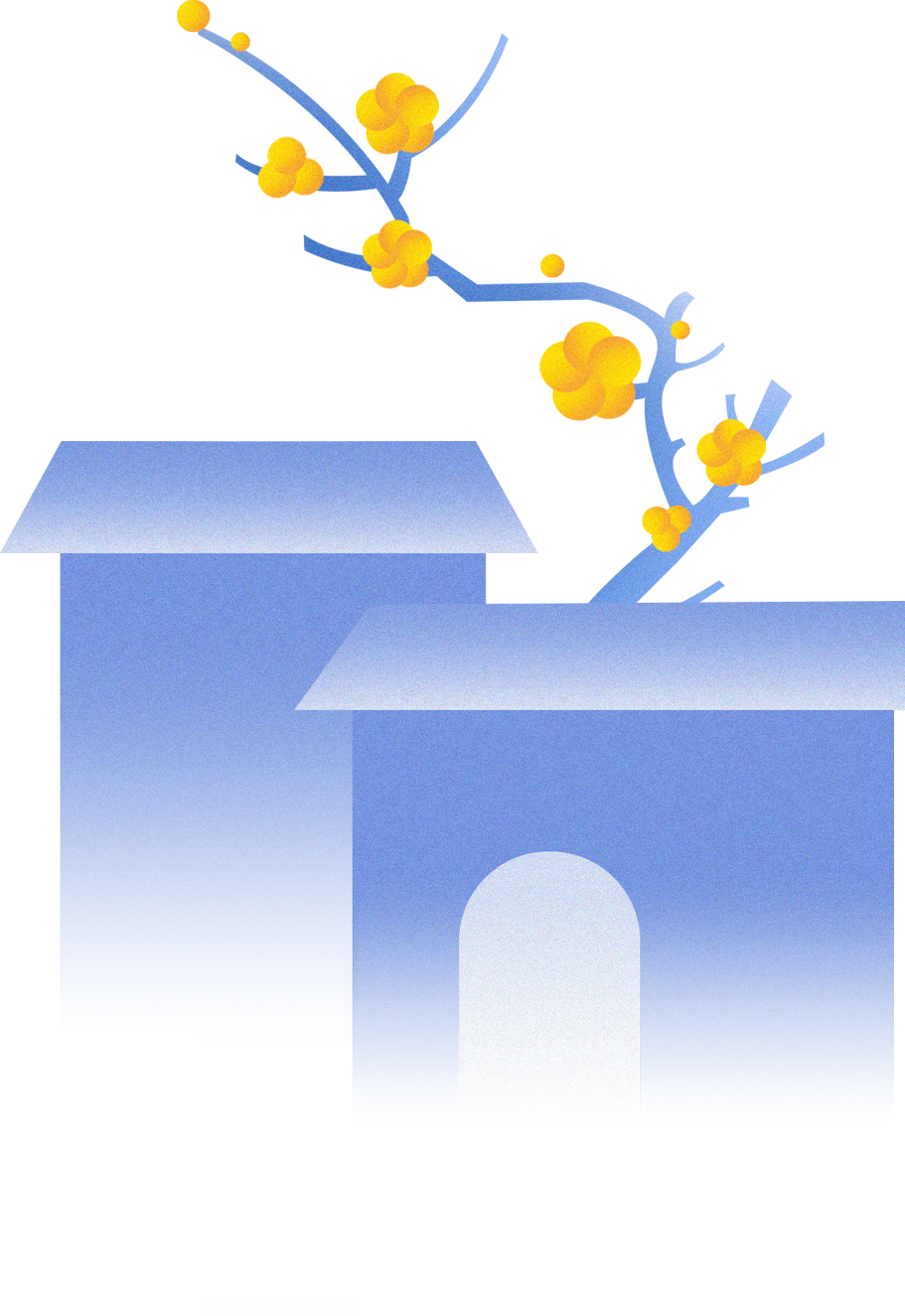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张亚萍
立冬的第一天,淅淅沥沥的小雨却一直下个不停,淋得人心底也泛起几分湿冷,忽然特别想念儿时冬日里那实打实的寒与暖。
儿时的冬天,是由凛冽干爽的寒风、漫天飞舞的大雪、香甜酥脆的麻糖和冰凉甜蜜的冻柿子组成的,而那冒着橘红色火苗的火炉和蓝天白云映衬下红彤彤的阳光,则是记忆中冬日最温暖的画面。
每到屋里生起火炉,我们开始穿着棉袄棉裤上学的时候,小巷里就会响起卖麻糖的吆喝声。卖麻糖的小贩通常是上了年纪的老汉,他们身穿一件没有外罩的白茬皮袄,头戴一顶厚厚的棉帽子,那白茬皮袄大多数时候又黑又脏,几乎都看不出原来的底色了。小贩的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里面放着实心麻糖、红麻糖、灌馅儿麻糖、麻棍等多个品种,上面用白布盖着,不论天气有多么寒冷,都能在萨拉齐城里的大街小巷听到他们清脆悠长的叫卖声:“麻——糖——哎!灌馅儿大麻糖哎!”对于当年物质匮乏生活困难的我们来说,酥脆香甜的麻糖就是平日里很少吃到的美味零食了。那时候的实心麻糖二分钱一根,灌馅儿麻糖五分钱一根,我那时没有什么零花钱,每次只能拿一毛钱买五根普通的,或者买两根带馅的,馅是用炒熟了的黄豆磨成的面做的,特别香甜。有时候姥爷会一次给我们买上几斤麻糖,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来点儿,放在家里让我们慢慢吃。
麻糖也可以用小米去换,至于兑换的比例我就记不清楚了。那会儿我家住在萨拉齐城西,离做麻糖的作坊不是很远。我现在还记得和妹妹不顾寒冷,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帽子和手套,欢天喜地地捧着小米跑向麻糖作坊。主人一般也很懂小孩子的心思,我们换到手的麻糖总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满足了我们不同的口味和需求。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各自拿出一根来品尝,我吃带馅的,她吃红麻糖,一路上有说有笑心满意足地向家里走去。
麻糖还能作为人们日常娱乐的一种项目,俗称“打麻糖”。两个人各挑一根麻糖从中间掰开,比谁的窟窿眼又粗又多,谁就赢了,输的一方就要付买麻糖的钱。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姥姥院里的几个小伙子玩“打麻糖”的游戏,赢了的人总是很慷慨地把麻糖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我没少跟着沾光。那样一根小小的麻糖带给童年的我们多少快乐和满足啊。而如今,那份简单的快乐和满足早已被时光稀释,不论是那个纯真的年代,还是我们幸福单纯的童年都一去不复返了。
冻柿子是我童年记忆中冬天唯一能够吃到的水果。它皮薄汁多,甘甜冰爽,那橙红色胖墩墩的色彩和模样,在单调萧瑟的冬天里显得格外喜庆,让人心头不由得产生无限欣慰和暖意。将冻柿子泡在凉水盆里,过一阵里面的冰就会析出来,此时的冻柿子拿在手里软软的,只需轻轻撕开一点儿皮放在嘴边一吸,那又甜又黏又冰的汁水就会从嘴角一直甜到心里。当那甜甜的汁水从喉咙慢慢滑进胃里的时候,那冰凉爽滑的感觉让人浑身都有说不出的畅快和惬意。除了汁水以外,冻柿子中间还有好几个舌头一样的软片,咬上去又脆又甜,是整个柿子的精华所在,也是我最喜欢吃的部分,吃完后总会对那美妙香甜的滋味念念不忘。
我家在清真寺对面的二道巷居住的时候,院里的邻居张爷爷是商业综合公司的老职工。张爷爷个子不高,精瘦干练,虽然那时候已经退休多年,但是每年冬天都要与人合作从河北往萨拉齐拉好几车冻柿子批发。因为有这样便利的条件,妈妈没少从张爷爷那里给我们买冻柿子,甚至有些脱了皮的或者长得不好看的,张爷爷就免费送给了我们,所以那些年里那金黄冰凉的冻柿子确实在冬天给我们姐弟解了不少馋。直到现在,每年冬天我都要买好几次冻柿子,吸着那冰凉香甜的汁水,就会想起小时候吃冻柿子的种种有趣场景。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如今超市里四季瓜果琳琅满目,孩子们的零食更是五花八门,但那根二分钱的麻糖和那个需要用凉水“拔”一下的冻柿子,却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代表着那个物质简单却情感丰沛的年代。
橘红的炉火、湛蓝的冬阳、清脆的吆喝,还有那舌尖上冰凉彻骨的甘甜,共同编织成我心底最温暖、最柔软的冬日念想。它们提醒着我,无论季节如何交替,岁月如何寒冷,最暖的冬日,从不是艳阳高照,而是藏在回忆里的那些人、那些味,岁岁年年,温暖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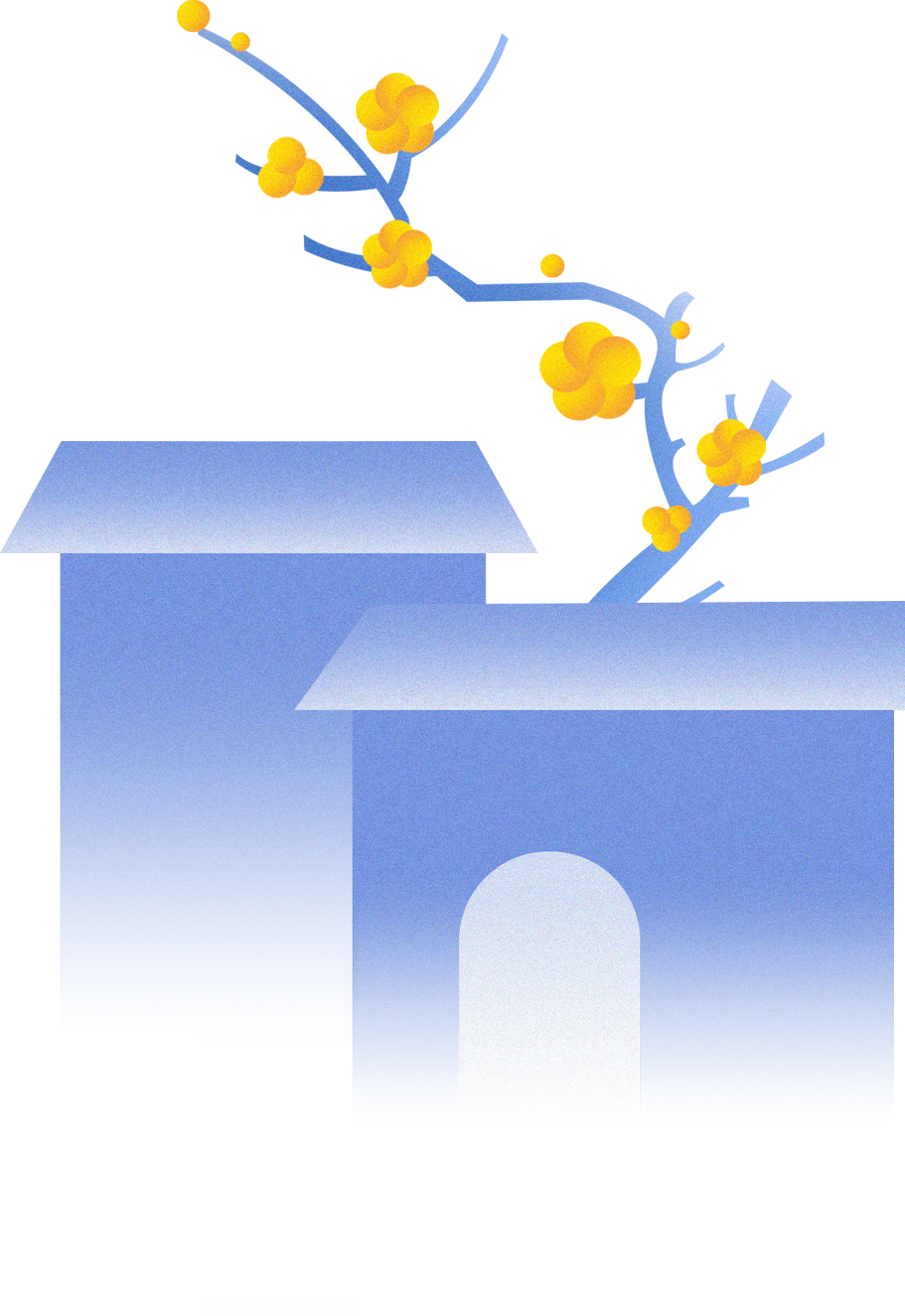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许颖
十一月进入初冬,天气渐渐凉下来了,但包师院夜市的热情未减,腾腾的热气顺着摊贩小车升到上空,将这幸福的烟火人间紧紧环抱。
从到达第一个小摊开始,包师院夜市长长的队伍就在眼前铺展开了。各式各样的霓虹灯光牌让人眼花缭乱,眼神一时间失了焦,不知道该看哪个好。田记蛋堡、浇汁豆腐、眼镜烤冷面……我贪婪地想一览看尽所有的摊位,可发现这繁华的巷子像一根射线似的没有尽头。
一转头,一排精致的冰糖葫芦小车呈现在我面前,今年的冰糖葫芦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吃商极高的摊主们研究出了许多组合样式的糖葫芦。奶油色的干噎酸奶点缀于绿色的青提中;菠萝蜜夹着草莓一起倚靠在长条奶皮子上;山药豆与蓝莓的奇妙组合被薄薄的糖围绕着;还有人们期待已久、味道浓郁的榴莲糖葫芦。正宗的圆山楂与经典的扁山楂虽仍是糖葫芦摊的老嘉宾,但好似它们已稍逊一筹,一个个都落寞地站在“爆款新品”身后。我凑近小摊去挑选,像是参加了一场彩色的水果盛宴。看着下面的价格大都已是12元以上,不觉想起初中时3元一串的橘子糖葫芦是那么物美价廉。薄薄的糖下是冰凉的橘汁,一口下去,清凉甜蜜的感觉从心里喷涌而上。
我和朋友聊起了糖葫芦,忽地想起了小学课本里有篇讲糖葫芦的文章,叫《万年牢》。小时候好像没太读懂,只记得在讲糖葫芦的制作过程,怎么均匀蘸糖,后来才明白了这篇文章的用意,坚持自己正确的准则,做人做事凭良心,认真做好每一件事,这就是万年牢。
一切事物都在快速发展,糖葫芦也不例外,老式扎草堆的糖葫芦摊好像慢慢走出了我们的视野,随之迎来的是装饰精致、种类齐全的出片儿糖葫芦。我也渐渐长大,从家乡的小镇出来,来到了异乡上大学。旧的、熟悉的事物在逐渐远去,我开始面对着新的、陌生的一切。我曾看到网上说,老式糖葫芦像是街巷里消失的一束花,那儿时记忆里的这一束花,也娓娓带走了我的童年。
再往里走,就看到一条“贪吃蛇”队伍长长地包围了伊伊麻糍店,人们毫不在乎通红的脸和紧紧缩在袖子里的手,千辛万苦只为尝到那一口期待已久的美味。我没有停留太久,直直奔向那最让我惦记的田记蛋堡。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妻,配合得像左右手一样默契。丈夫专注地翻动着铁板上的蛋堡,滋啦作响的油花溅起,暖黄色的灯光照在他充满细汗的额头上,也照出了他眼角的细纹。妻子则负责装袋,收款,抬头递出食物时,总会送上一个朴实的、带着暖意的笑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温和地说:“小心烫,拿好喽。”等待的间隙,我听到旁边熟客的搭话,才知他们这摊风雨无阻已摆了好几年。我忽然觉得,手中这枚热乎乎的蛋堡,滋味变得更厚重了,那脆壳之下,包裹的或许不只是鸡蛋和肉馅,还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与对生活的热爱。我不觉想起家乡的人们,那些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干的乡亲们。
刚过清晨五点,西土产已站满了人,三四十号的人早已簇拥在了一起,焦急地等待着雇主的到来。军绿色的裤子沾染着昨晚夜归溅到的泥点儿,不合脚单薄的鞋子,头顶上过时的黑色老头帽好似他们的标配,一手拿着冻得硬邦邦的白馒头,一手拿着从家中灌来的热水。一辆面包车来了,他们奋然起身,向雇主展示着自己的个头与力量,渴望用自己的汗水与力气谋得营生来维持生计,他们压着价争先恐后地向前走去,随后三言两语敲定了下来,中年男人用冻得通红皲裂的手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诉说着找到营生的喜悦,嘴里哈着白气,也不忘用别扭的口音说着晚上回去给小孩带吃的。他们睫毛上的冰晶一眨一眨像闪着金光,清澈的目光像是饱含着泪花,没有知识与文化只能靠着体力为生,只能每天“站桥头”找工作,没有对先天条件与命运不公的抱怨,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信念。在那个地方,许多孩子就是这样被供出来上大学的,我也不例外。“你愣着干嘛,怎么还不吃啊?”朋友的话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一口下去,肉蛋煲让我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味道中带着淡淡的幸福感,更带着一种坚毅与力量。
不知不觉,已经快要22点了,可还有几家没有逛完,夜市来往的人仍川流不息,有本校的学生,也有刚下班赶来的职工,还有远道而来特意品鉴美食的人们。后面的芝士火鸡烤冷面、广东肠粉还等待着我,但门禁时间快到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和夜市道了个别。走到巷口,回望远处是彩色的荧光灯亮不绝,大家说着笑着,吹着风,在喧嚣与飘香交织的夜市里享受着此刻,忘掉一切。包师院夜市仍然热闹,仍然繁华,这是大学里最平凡的一天,日后或许也会成为让人怀念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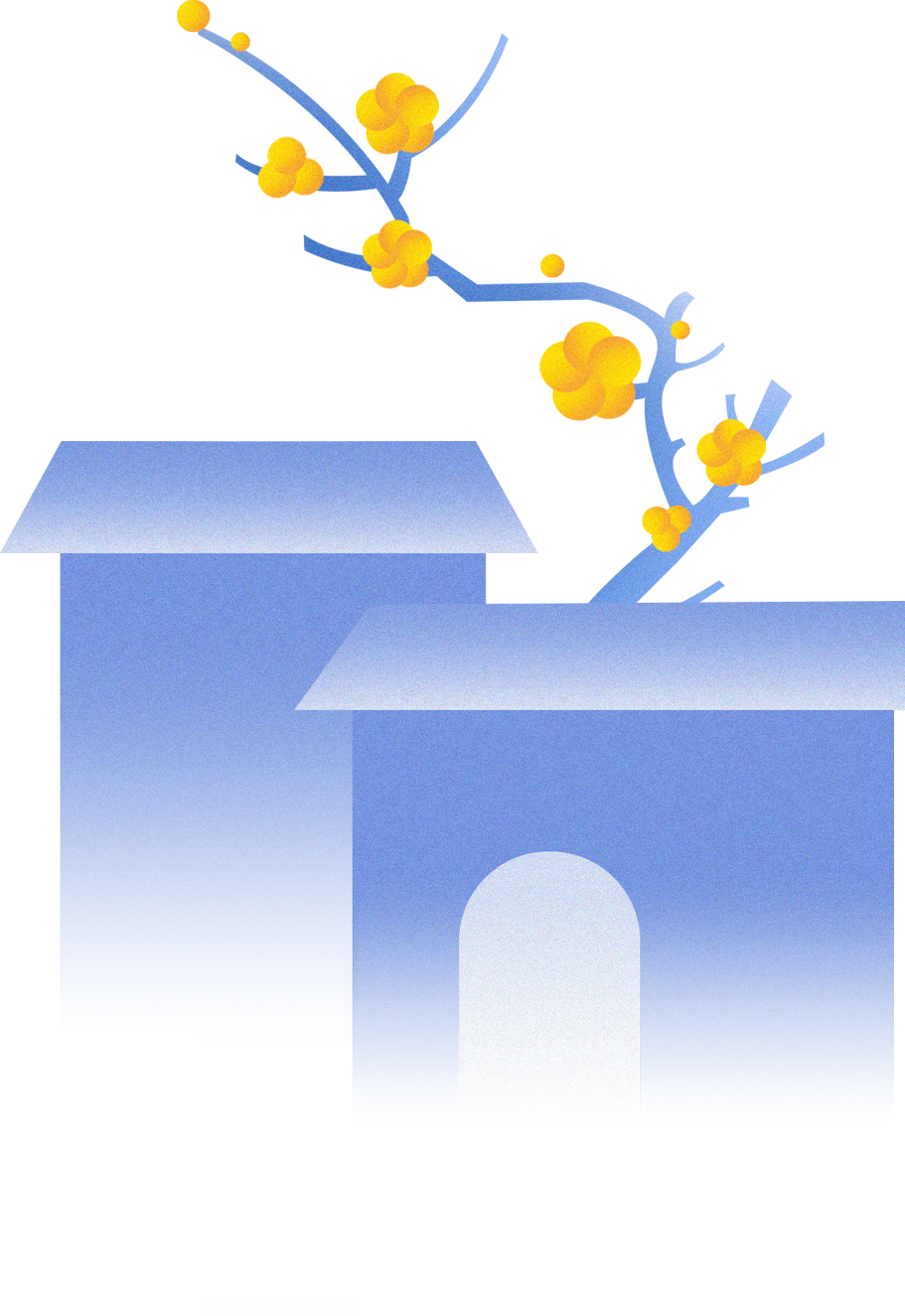
作者 / 王芳
前几天路过街角的糖炒栗子摊,甜香飘过来。风里的甜意还是熟悉的味道,却少了那个会把栗子塞进我嘴里的人。
看着女老板手握长柄铁铲,翻砂的动作熟练又稳当。栗子在锅里慢慢变了模样,原本深褐的壳渐渐裂开小口,露出里面浅黄的果肉,热气裹着甜香从裂口钻出来。我站在摊前等,看她时不时弯腰,用铲子拨开砂粒,拣出几颗裂得正好的栗子,丢进旁边的竹筐里。多年前,父亲,也曾像我这样驻足栗子摊前……
泪水模糊了眼睛,心里一阵阵酸痛,想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思念却无处不在,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关于父亲的记忆撞个满怀,离开越久思念越深的痛,只有自己懂。
作为支援包钢建设的老工人,父亲十六岁就从老家来包头,为了能进包钢当工人,硬把年龄报大了两岁。招工人看着他又瘦又小的模样犯嘀咕,可他还是攥着拳头留了下来。三班倒的日子熬人,饭总吃不安稳,胃病就这么缠上了他,后来的岁月里,药瓶和工服几乎成了他的标配。可再苦再累,丝毫没有影响父亲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女的关心。
父亲上班拎一个带饭的小黑兜,他下班回来总能从兜里给我和姐姐掏出点儿好吃的。有时是裹着糖霜的山楂条,有时是红彤彤的海棠果、软糯的桃肉干,都是他在下班路上特意买的;冬天则有炒得喷香的瓜子、花生以及糖炒栗子。他会坐在床边,捏开栗子壳,把金黄的果肉递到我和姐姐嘴边。
记得那年春节即将来临,父亲由于加班好几日没有回家。每到吃完晚饭,我和姐姐就到胡同口看看,连续几日都失望而归。那日,父亲忽然回来了,从他那小黑兜里竟掏出一袋子热乎乎的糖炒栗子,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天栗子买得多,让你们吃个够。我伸手去接纸袋,指尖触到滚烫的温度,还能听见栗子在里面轻轻碰撞的声响。听到母亲责备他乱花钱,父亲却说:“给孩子们花,舍得。”我慌忙抱着栗子跑进了屋,然后把剥开的第一个热乎乎的栗子喂到了父亲嘴里。
也就是那个冬天的春节,父亲住进了医院,由于急性胃穿孔。手术切掉了他三分之二的胃,可他却很坚强地挺了过来。顺利出院后,由于在家休养,父亲总会溜达到街角的栗子摊买糖炒栗子。那日,他气喘吁吁回到家,母亲赶紧扶他坐下,责怪他生病还往外跑,他却摆了摆手,说:“孩子想吃……我去的时候排队,怕凉了,就揣在怀里焐着。”下班回家,我打开油纸包,每颗栗子都还带着余温。他看着我剥栗子,带着微笑说,趁热乎,赶快吃。为了买这袋栗子,术后身体虚弱的父亲从小区走到街口,几乎是走走歇歇,而他揣在怀里的,何止是一袋栗子。栗子在嘴里慢慢化开,甜意裹着暖意,却让我鼻尖一阵发酸——原来父亲的爱,从不会因为病痛而打折扣,只会悄悄藏在每一个他记挂的细节里。
21年了,街角的栗子摊换了一个又一个,可我再也没吃过那么甜的栗子——不是味道变了,是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把栗子揣在怀里焐热,会把果肉剥好递到我嘴边,会把日子里的苦都自己扛着,只把甜一点儿一点儿攒进小黑兜,给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暖。
如今再路过栗子摊,我还是会买一袋,像当年父亲那样,慢慢剥一颗放进嘴里。甜意漫开的时候,就好像还能听见他说“趁热吃”。还能看见他坐在床边,手里捏着栗子,眼里装着我们。原来父亲从没有走远,他把爱藏在了那袋焐热的栗子里、藏在了小黑兜的惊喜里、藏在了每一个想起他的瞬间——那是他留给我们的,一辈子都化不开的甜。

(编辑:吴存德;校对:黄韵;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