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至凛冬,冬至已至。
这是北半球白昼最短、夜色最长的一天,却也是盛满人间暖意的日子。对包头人而言,冬至从不是单薄的节气符号,而是浸着烟火气的生活记忆。它藏在老厂区邻里围坐的餐桌旁,是一盘鲜香四溢的羊肉馅饺子,蒸腾着岁月温情;它飘在清晨街巷的早点铺里,是一屉热气腾腾的稍麦配醇厚砖茶,唤醒冬日活力;它融在三代人相守的时光中,是一脉相承的老习俗,延续着独属于鹿城的冬日浪漫。
寒尽春生,冬至后,暖阳渐归。愿这一日,你我皆有美食暖胃,有爱意暖心。
——策划 姬卉春
作者/王平
终于等来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土默川的冬天真正拉开大幕。
“立冬不死牛,还耕十亩地。”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标志,但土默川的农人们,却扶着犁耙翻起油黑的土,碎土块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犁过的土地在松软中,等一场雪来焐热墒情。
小雪来得轻,被风一吹便无影无踪。虽然风里有了些许凉意,但碾磨坊的隆隆声却热闹起来。石磨转着岁月的圈,玉米碾成金黄的粒,糜子落进笸箩,麦子被磨成雪白的面粉。女人们的围裙沾着面星子,男人们满脸凝着汗,孩子们在磨道旁追着毛驴跑。这是土默川秋的尾章,把最后一缕温热揉进人间烟火里。
真正叩开冬门的是大雪节气,却没有一点儿下雪的前兆。猪的一声哀嚎唤醒了村庄。案板上的猪肉不消一刻便挺成僵硬,大铁锅里的水滚着白汽,混着蒜醋香漫过村庄。三婶往灶里添把柴,火星子噼啪炸响;三伯早举着酒碗喊“六六顺”,皱纹里盛着满足;连平日里寡言的三爷爷都凑过来,用缺了齿的嘴啃着骨头……年的气味就这样弥漫开来。
土默川的雪是有信的,它踩着节气的鼓点来。大雪节气刚过,一场酝酿多日的大雪便悄然而至。初时是碎玉,落满柴垛与檐角。再落便成了鹅毛,把山染成素帛,为平原盖上棉絮,连干树枝都缀了晶莹的冰坠子,风过时像风铃作响。
窝在屋里的我们等玻璃窗上的冰花次第绽开。无法想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怎样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神奇的童话世界。冰窗花有时像一片丛林,各种树木疏密有致,层层叠叠,林间有跳跃的松鼠,还有散步的喜鹊。有时又像一个神秘的海底世界,小鱼小虾游弋其中。有时又像崇山峻岭,又像深邃的太空。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暖融融地照在玻璃上,美丽的冰窗花转眼间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但对不可预知的明天却是又一种崭新的期待。
白雪覆盖下的村庄,猫冬的汉子们围炉煮酒,酒碗相碰时说的不是营生,是当年一起偷瓜的趣事;媳妇们盘腿坐炕头,绣花的针脚密得像心事,聊的是东院新娶的媳妇会不会过日子;更有那爱唱二人台的,嗓子亮得能穿透雪幕,“正月里来是新春”的调子一扬,连门槛上的猫都支棱起耳朵。
孩子们缩着脖子扫开一片雪,露出黄褐色的地,撒把糜子便蹲在墙根。流着清鼻涕的小子屏住呼吸,见麻雀扑棱棱落下,猛地拽动套绳,原来生存的法则,在童眼里也带着天真。可土默川的冬从不是冷的,屋外的雪落得静,屋内的火却烧得旺。猫在灶前打盹,狗蜷在脚边暖爪,男人醉了拍着炕沿唱《走西口》,女人笑着拧他胳膊。
冬至那天,夜长得像一根扯不断的线。游子的脚步踩着路上的薄冰,背包里装着给爹娘的降压药、给孩子的新棉鞋,还有一句憋了一年的“我想家了”。父亲坐在热炕头,见我进门,指着桌上的饺子:“冬至的饺子要捏严实,不要漏了福气。”我数了数,他只吃了三个,五岁的曾孙却扒拉着吃了七个。
大寒是冬的终章。“该冷不冷,不成年景”,西伯利亚的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刮得人脸生疼。可田婶家的小儿子偏选在这日娶亲,红盖头映着雪光;鹤发童颜的二伯却在晨起时合了眼,安详得像睡觉;赵奶奶抱着重孙笑出了泪,二锅头的香气漫过宴席,倒像是给生死接了个场。原来无常是常,有常是无常,就像雪落了又化,化了又落,不过是换个模样守着这片土。
腊月的雪一场接一场,旧雪未消新雪又至。父亲的身体渐渐沉了,像片落在雪地上的枯叶。他不再能陪我煮雪品茶,却总望着窗外说:“每片雪花都不一样,来过,落过,就够了。”大寒夜的风撞着窗棂,我握着他凉透的手,看一盏凡灯灭了,却见满天星斗亮了起来。
土默川的冬,原是一场关于轮回的故事。每一片雪都写着“活着”的分量,每一缕炊烟都续着“归根”的暖。我们在这冷冽里焐热日子,种下希望,把生老病死看成节气的韵律,把聚散悲欢酿成岁月的酒。
所谓冬,从来不是萧索,是生命最本真的热望,来过,爱过,守过,便不负赴一场雪色倾城的土默川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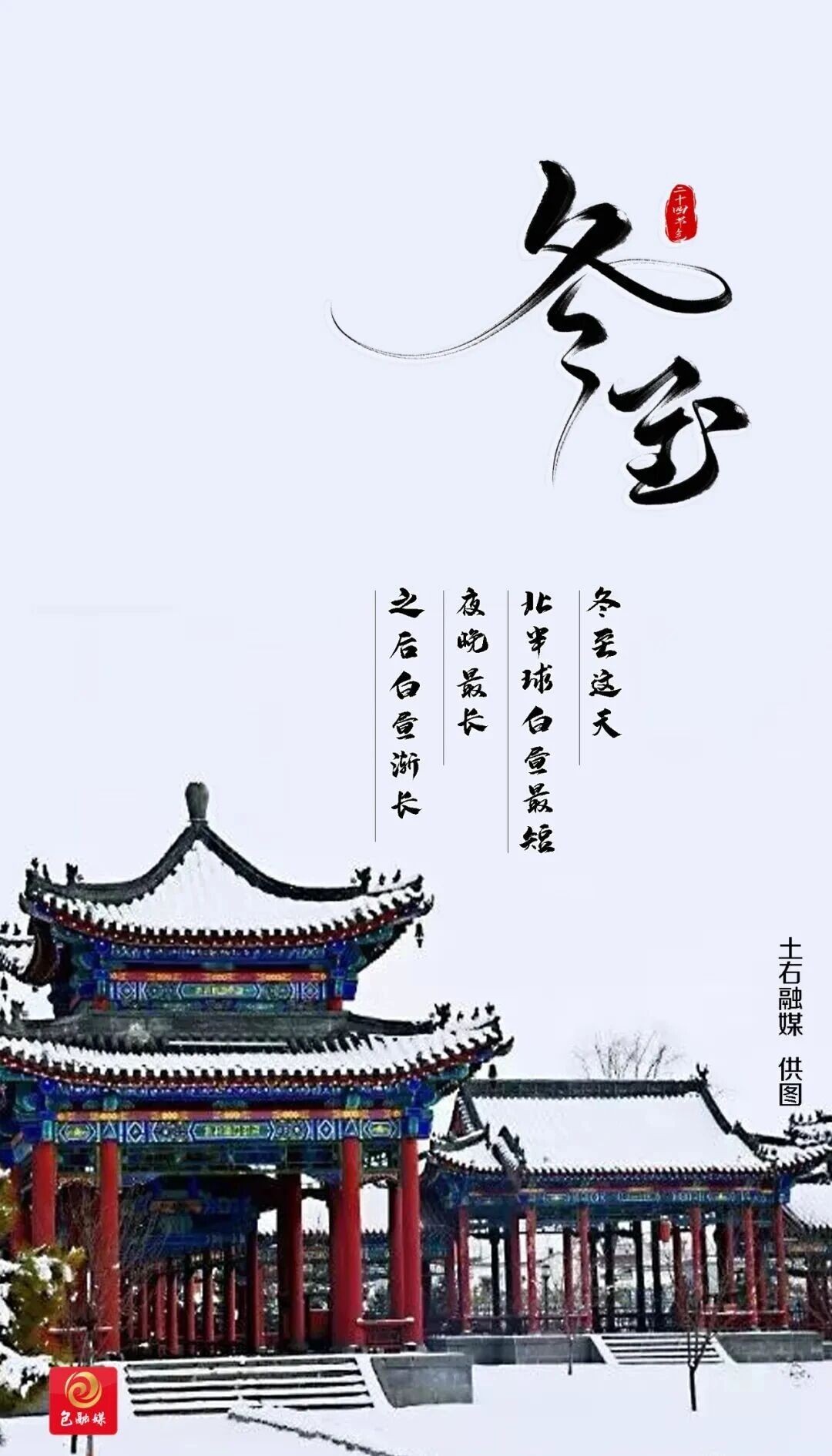
作者/刘东华
冬至大如年的记忆都与妈妈相关,是她用实际行动让我知道,生活除了吃饱穿暖,还得有仪式感。
每个冬至清晨,都在妈妈“快起来,今儿冬至,有好吃的”叫声中醒来。火炉已烧旺,上面的铝壶正“突突”喷着白气。炉火旁烘烤的衣裳,妈妈摆得极有章法:最下层是厚重的棉裤棉袄,往上依次是线衣线裤,而最贴近那红红炉火的,必定是贴身的秋衣秋裤。那熨帖的温暖,既一丝不苟,又有仪式感。
我们洗漱时,妈妈会冲油茶面。那是用猪油将面粉炒到焦香,开水一冲即成的糊糊。一个“茶”字,倒给这浓稠的碳水添了份清雅。与此同时,妈妈还会在大灶上烙“歘煎”,即摊煎饼。“歘”是象声,是面糊滑入滚油那一瞬的欢快;“煎”是动作,是耐心等候其成的笃定。一张金黄油亮的煎饼在手,就着油茶面下肚,元气便从胃里升腾起来。
寻常的日子,妈妈给我梳头总是利落的马尾。唯独冬至这天不同。她会拿出一方崭新的红纱巾,三折两叠,手指翻飞间,一朵生动的大红花便绽放在她掌心。那时的头绳,不过是秃秃的橡皮筋,这朵红纱花,便是顶奢侈的装饰了。她仔细地将花系在我的马尾上,我对着穿衣镜左照右照,心里美得冒泡。再郑重地系上压在枕下一夜、叠得棱角分明的红领巾。镜中的女孩,神气活现,仿佛这隆冬的节日,有一半是因这头上的红花而光亮起来的。
领着睡眼惺忪的弟弟上学去。为了给他醒神,一路上专找结了薄冰的地方打出溜滑。到了校门口,总能看到抱着引柴的同学。那时的教室是平房,值日生得自己生炉子。炭由学校供给,引柴却得从家里带。刨花、树枝、旧报纸,什么都有。生炉子是门大学问,先放软柴,再架硬柴,最后小心地添上炭,从下面点燃。弄得不好,浓烟倒灌,熏得人眼泪直流,甚至燎了眉毛头发,也是常有的事。但等到两个炉子都烧旺了,橘红的火苗欢快地舔着炉壁,那份由自己亲手创造的温暖,便格外珍贵。常有同学将冰冷的馒头、花卷放在炉盘上烤,不一会儿,麦香混着烟火气,便在教室里弥漫开来,这是那些岁月里,最扎实的富足感。
中午的冬至盛宴,主角是酸菜油渣馅饺子。油渣,我们叫“油滋锁子”,是肥肉炼油后剩下的精华,黄澄澄、香喷喷,缩成一个个酥脆的小“锁头”,锁住了全部的荤腥与香气。妈妈拌的馅,咸淡适中,油润喷香;擀的皮,中间厚四周薄,筋道无比。一口咬下去,酸菜的爽脆、油渣的酥香、面皮的麦甜,在口中交融。佐着蒜泥和老陈醋,真有那种“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的酣畅淋漓。
除了饺子,桌上还常有两样:醋熘白菜、小葱拌豆腐。白菜酸爽开胃,豆腐一清二白。这菜蔬来自姥姥姥爷家,面是姥爷磨的,菜是姥姥种的,连换豆腐的黄豆,也是姥姥给的。这顿冬至饭,吃出了一份血脉亲情的暖意。
若妈妈手头宽裕,还有泡在凉水里的冻柿子和海红果。咬一口冻柿子,那蜜一般的甜浆凉丝丝地滑入喉中;海红果则是酸甜的,格外醒神。若妈妈得闲,晚饭时还会用胡萝卜熬一小锅糖稀,做一笼蒸饼。我最爱将饼一层层撕下,卷成小卷,蘸着糖稀吃。松软的饼,清甜的糖稀,那种丰腴的满足感,甭提有多美了。
吃喝完毕,妈妈会为我变个新发型:梳两只羊角辫,戴一顶她自己织的红线帽。帽子是用父亲劳保手套拆线、染色后,用繁复的松紧针法织成的,厚实又好看。说起编织,妈妈可是出名的巧手。她总爱琢磨新花样,我们毛衣上的花样,比商场里的还精巧。毛裤织得极厚,是我上体育课的优势。那时我们常去东河槽滑冰,有时会坐在纸壳上连成串从冰坡上滑下,有时会两人拉着一个蹲下的人在冰上飞奔。那时的孩子仿佛铁打的,磕碰摔跤,爬起来照样疯玩。
论玩,最有趣的还是踢毽子。冬至前后,妈妈有时会宰一只鸡,那最艳丽修长的尾羽,便成了我们毽子的材料。一个铜钱,包上布,缝上一截细管,插上三四根光彩夺目的鸡毛,一个漂亮的毽子就诞生了。冬天穿着厚棉鞋踢毽子,脚不疼,毽子起落翩跹,是灰白天地间一抹灵动的色彩。
其实,冬至大如年,大就大在这份郑重其事的“过”上。是妈妈,用朴素的仪式,为我们冬日的岁月,镀上了一层抵御严寒的暖光。

作者/赵成祚
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像是关上太阳光亮的信号,刚响完,暮帘便“哗”地一声倾泻下来,迅速吞没了天桥街道和楼宇建筑的轮廓。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汇入校门口穿着冬袄、呵着白气的人流。汽车的尾气混着冰碴子,钻进鼻腔,有种工业城市冬天特有的、冷而硬的味道。
再过两日便是冬至,脑海里响起地理老师讲课的声音:“……冬至日,太阳行至最南端,北半球夜最长、昼最短。”我望向车窗外飞速倒退的、光秃秃的行道树,心想,我们这座城市,包头,几乎就是最短白昼的北端尽头吧。
去年冬至,放学到家时,楼房的窗户中已然亮起灯光,细看每一家也是不同的颜色,那最温馨的,便是从我家散发出来的。推开家门,一股暖意便扑面而来,不是暖气片干燥的热,而是湿润的、带着浓郁食物气息的暖流,像一层柔软的羊绒毯子将我裹住。那气息的核心,是面皮与馅料在沸水中交融后特有的、朴素而丰盈的麦香,混合着肉馅与葱姜的鲜美,让人无比温暖与安心。我仿佛能“看见”那锅汤在厨房里沸腾的模样——无数只“小白鹅”在水浪中沉浮翻滚,饺皮渐渐变得晶莹透亮,隐约透出内里饱满的馅色。
妈妈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梭,餐桌上已摆开阵势。几个青花瓷盘里,分门别类地盛着不同馅的饺子:元宝似的是传统的羊肉大葱馅,略弯月牙形的是爸爸爱吃的酸菜粉条馅,还有几个花边精致的是给我包的虾仁三鲜馅。妈妈正将最后一盖帘饺子端上桌,那饺子个个肚儿滚圆,挺立在撒了薄面的帘子上,像一队待命的雪地士兵。“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她笑着用一句老话招呼我。这是包头的冬至,一个汉地谚语与北疆风味在此地达成奇妙和解的夜晚。羊肉馅是草原的馈赠,酸菜馅是东北的乡愁,虾仁馅是父母的疼爱,一同在这张方桌上水汽氤氲。
然而,最触动我的,并非这桌子“满汉全席”。饭前,爷爷默不作声地走向阳台。我跟过去,看见他对着北方——大概是阴山乃至更辽远草原的方向,摆上一只小瓷碟,碟中是三只煮得最为饱满端正的羊肉馅饺子,旁边是一小碟醋和一杯清茶。没有焚香,没有祷祝,他只是静静站了一会儿,斑白的鬓角在窗外万家灯火的映衬下,像落了霜的草。北风拍打着窗户,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遥远的回应。
爷爷是当年从农村走进钢城的一代人。他很少讲述老家,但他的许多动作里,住着另一个世界。此刻这无声的祭奠,与资料里那庄重的“祭拜长生天”的仪式,内核是相通的。那不是迷信,是一个曾将命运寄托于长生天与先祖护佑的民族,将最深沉的感激与敬畏,凝练成了日常的仪式。饺子是最朴素的敬献,清茶是最本初的洁白。他在用这极简的仪式,与一个更浩瀚、更沉默的时空对话。城市的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那影子竟有几分像风中坚韧的牧人。
饺子蒸腾的热气,驱散了玻璃上的寒霜。我们围坐,大快朵颐。滚烫的饺子蘸着老陈醋,酸香瞬间唤醒味蕾,随即是馅料丰腴的汁水在口中迸发。羊肉馅的醇厚、酸菜馅的爽脆、虾仁馅的鲜甜,各种滋味在舌尖上交织。爸爸说起他小时候,冬至日小区里也会有小小的聚会,各家拿出看家本领包饺子,山东的鲅鱼馅、河北的猪肉大葱馅、本地的手工羊肉馅,在饭桌上开起了“饺子博览会”。掰手腕、顶杠子之后,便是品尝与点评,笑声能震落屋檐的冰棱。草原的豪迈与中原的精细,在此刻的餐桌上水乳交融。
电视里播放着新闻,而我的思绪却飘向窗外漆黑的夜空,飘向地理书上那条无形的南回归线。此刻,太阳正在那个遥远的最南点徘徊,将最吝啬的光热给予我们所在的北地。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学会了向内部索取温暖。这温暖,在沸水中翻滚的饺子里,在妈妈捏合的每一个褶皱里,也在血脉里那份面对漫漫长夜时,既不抱怨也不颓丧的、安静而蓬勃的耐寒力。
夜深了,我站在阳台与爷爷并肩。城市是一片光的海洋,吞没了所有星斗。但我知道,在灯光照不见的北方,是沉睡的阴山,是北方冰雪覆盖的草原。它们都在这至暗至寒的夜里,静静等待着那个必然的、缓慢北归的太阳。而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夜晚,所有围坐的欢喧、所有安静的缅怀、所有下咽的温热,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宇宙规定的漫长寒夜里,用最朴素的面粉与最真挚的心意,为自己捏起的、一盏盏小而坚实的光源。
作者/李春
真正的冬天
到了
站在最短的白昼里
迎接最漫长的黑夜
笑数三九
成了指间
最浪漫的动作
寒霜染须
眉白如雪
仲景的舍药
补得冬天
阳气腾腾
我站在
赤道之北
漫画着
那个久远的梦想
眼前的山河
仿佛传来了
滚滚的咆哮
春天的鼓点
铿铿锵锵在
柳芽抽丝花苞绽放中
袖着手
捂着耳的山乡
年味儿扑鼻而来
闷酒中
我依稀听到
亲个蛋蛋的山妹在提醒
告诉你个事
明天是冬至
别忘了
吃饺子

(编辑:吴存德;校对:霍晓霞;一读:张飞;一审:张燕青;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