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至,年味浓,许多人在快节奏生活中感慨年味儿渐淡,而藏在时光里的旧岁光景,总能勾起最柔软的乡愁。对老包头人而言,最深的年韵,在腊月寒风里,在母亲灶台的烟火中,更在厂矿家属区邻里相亲的温暖岁月里。
那是寒冬里炸麻花、炸糕的香甜气息,漫过大杂院的窗棂街巷;是扫房、蒸馍、写联、贴福的忙碌欢喜,邻里相帮,暖意融融;是雪地鞭炮的响亮,是新衣针脚里的温柔,是阖家团圆、邻里欢聚的融融温情。
三篇怀旧随笔,带你重回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包头,重拾烟火缭绕、邻里无间的地道年味,在文字里穿越时光,重温刻在心底的中国年。
——策划 姬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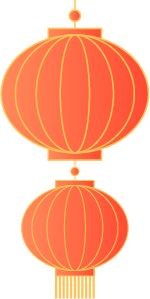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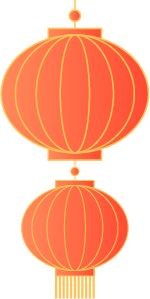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作者/杨丽英
母亲打电话来宣布:这周末炸麻花,让我们回去帮忙。
母亲年龄大了,楼房里小锅小灶不方便,我们总是劝她去外边买点尝尝算了,省得油烟火燎,费时费力。看来今年是劝不动了,时隔多年,我还真的特别怀念儿时腊月做年货的时光。
儿时,冬天格外的冷,刺骨的风像藏了针似的,拾筐柴火、提桶水,甚至是跑出去关个大门,脸和手都被冻得生疼。天地冻得硬邦邦,连狗叫声传出去,似乎都能被冻出一截脆生生的白痕。唯有“炸年货”的日子,这铁一样的冷就被灶膛里的火化开了口子。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这口子里透出的第一缕光,便是炸麻花。腊月的日子是掰着手指头数着过的,数到手指发红,数到心尖发痒,睡前不厌其烦地扒着门框问母亲:“明儿炸不炸?”
母亲的麻花向来是做得早的。一来我们上学可以当早点;二来炸出来的东西放得住,年下待客或是送人都从容;三来腊月里做年货的日子都是倒排的,耽搁不得。
炸麻花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地搬出那只沉甸甸的大陶瓷盆放好面粉,将水、油、糖用温水化开,和面、揉面。发面是悠长地等待,用厚厚的棉袄将面盆包裹起来,等到面团长得胖了一圈,轻轻一按,一个坑儿慢悠悠地回弹回来,便是时候放碱了。母亲拿出一团面,在抹了油的案板上反复地揉,揉到它韧性十足,再搓成长条,切成均匀的小剂子,整齐地码在白色的陶瓷盆里,一层剂子刷一层油,盖上盖子,让它们在阳光下变得更加柔软。
搓麻花时,左邻右舍的阿姨们会过来帮忙。醒发好的剂子温润得像绸缎一样顺滑,在掌心搓成细长均匀的条,对折,两头捏拢,顺势一提,那面条便自己绞成一个松散的扣。接着,一手捏住对折的环扣,另一手将两根面条向相反的方向轻轻搓动,搓紧了,再折成三折,那面条因着那股拧着的劲儿,自然而然地绞成六股,像小姑娘精心编起的发辫,匀称,紧实,又带着一种活泼的韵律。
我看得入神,央求着学,可面在我手里总是不听话,忽粗忽细,还会从中间断开。阿姨们看着我那“瘫软”的麻花缺胳膊少腿儿的样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帮着“整形”。我红着脸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搓,终于也能拧出个像样的麻花坯子了。母亲把我那些“作品”单独放在一边,炸出来,成了我独享的、带着自豪的零嘴。
大铁锅里,清亮的菜籽油泛起细密的波纹,第一根麻花顺着锅边滑下去,紧接着,第二根,第三根……“滋啦!滋啦!”声音稠密起来,连成一片欢腾的、滚烫的乐章。麻花坯子慢慢地浮上来,先是浅浅的鹅黄,然后便是金黄。母亲用长长的筷子轻轻地拨动,麦子被热油激发出的醇厚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又从门缝溜出去,吹散在腊月的风里。
第一锅麻花捞起,沥在铁丝笊篱里,阿姨们围过来“啧啧”地称赞这麻花做得好,母亲掰下一小截,吹一吹,尝一尝,笑容舒展开来:“真是不错呢,晾晾大家都尝尝。”刚炸好的麻花外壳是酥的,内里带着柔软的韧劲儿,麦香、油香,甜而不腻,足以抵挡冬日的寒冷和单调。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洒在一盆盆金黄的麻花上,热气在光线里舞蹈。
我的心早已飞到上学的日子里去了,往书包里揣上一根包好的麻花,走起路来都连蹦带跳,放学回家扔下书包直奔放麻花的陶瓷盆。一群冻得鼻子发红的孩子,聚集在巷子里比谁家的麻花拧得花儿好看,谁家的更酥脆。
记忆里,母亲炸好麻花,年味儿就来了,紧接着炸油饼、炸丸子、炸糕、炸猫耳朵、炸兰花豆……凉房里的大盆小罐都殷实起来的时候,年就到了。
我特意买了糕面和豆沙,期待着周末的炸麻花,一锅清亮的油,熟悉的“滋啦”声,藏在心底里的香甜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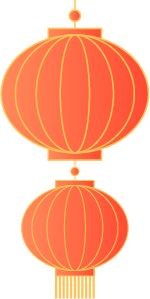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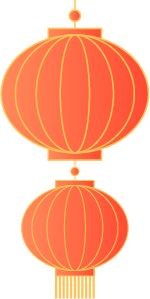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作者/刘东华
小时候,腊月的风刀子似的刮过包头的苍茫天地,卷起地上冻硬的雪粒,敲打着大杂院里每家每户的窗棂,却一点儿也吹不散院里那团愈来愈浓的、暖烘烘的味道。那味儿,不是单一的香,倒像是谁把所有的暖意、盼头、劳作与欢腾都揉碎了,混在一口看不见的大锅里,文火慢熬,蒸腾出满院丰腴的、让人心尖儿发颤的“年味儿”。
这年味儿,先是打各家各户的门缝窗隙里,袅袅地、争先恐后地溢出来。它有一股子油润润、热腾腾的劲儿。东家锅里“滋啦”一声,是油饼在滚油里胀开了圈圈涟漪;西家的笼屉上,白茫茫的蒸汽里混着新麦的甜香,那是暄腾的馒头出了笼。还有黄米炸糕,丢进油锅,便“咕嘟嘟”地吐出欢快的气泡,炸得外皮起了层脆亮的金壳子,里面却糯得能缠住牙。馓子细如龙须,在油海里翻滚成金丝网;炸丸子的焦香能引得院里的狗都趴在门口,鼻头湿漉漉地翕动。院角的空地上,支起了大铁锅,粗砂粒在锅里被炒得发烫,倒进饱满的花生与葵花籽,铁铲不停翻炒,噼里啪啦的声响里,混着坚果本身的醇香,飘得满院都是,大人小孩路过都要抓一把,嗑得满嘴留香。
熬煮另有醇香,是陈奶奶还是杜婆婆家熬的皮冻?肉皮在锅里咕嘟着,漾出黏稠的欢歌。酥鸡的酱香厚重,扒肉条的肉香酥烂,各家的铁锅铲子叮当作响,不同的油脂、酱料、食材在高温下碰撞、交融,煎炒烹炸,奏着一曲庞杂而和谐的灶间交响。香气们没了界线,拧成一股粗壮的、温暖的绳儿,拴住了整个大院。
我们小孩被香气喂养着、牵引着,在院里疯跑。年货的味儿是闻的,鞭炮的味儿,却是我们点亮的。
一个个小红鞭炮,被我们从整串的“筋骨”上小心翼翼地拆解下来,寻一处雪堆,将小红炮直直地插进去。对着手中的点炮香吹一口气,将亮起的红星对准捻子,旋即,“啪!”一声脆响,雪地上便绽开一朵小小的、红色的花,那股子独特的硝磺味儿,辛辣、鲜明、提神醒脑,猛地钻进鼻腔,直冲天灵盖——这是小孩的年味儿!
有时我们会扣个破铁桶在点燃的炮上,听那一声闷雷在禁锢中炸开,嗡嗡的余韵让人心满意足。更多时候,是捡拾那些“哑炮”玩。轻轻一掰,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火药,将两截断炮的火药头对头摆好,一点引子,两簇细小的、嗞嗞作响的火苗便猛烈对冲,迸出更浓的烟与更烈的味儿。还会将许多断炮围成一个“火药阵”,中心一点,刹那间便是一片细碎的“噼啪”火光,像一朵危险而绚烂的菊花。女孩子躲在屋檐下,看那些“魔术弹”“地转花”喷吐彩色的光轮。而我,却偏爱火柴擦燃时那一瞬的光与热,偏爱空气里久久不散的、令人安心的硝烟味。它不像花香果香那样易散,它沉甸甸的,落在棉袄的褶皱里,落在冻红的耳廓上,也落在记忆最深的年轮上。
当各家母亲开始长一声短一声地唤儿归家时,身上的火药味儿还未散尽。母亲从盆里拣出炸得最鼓的糕,从窗台外端回凝结得颤巍巍的皮冻,挟一块煎得两面焦黄的带鱼,让我们先“尝尝咸淡”。那混合着烟火气与人情味的丰腴,从舌尖一路暖到胃里。而比这滋味更让人心里踏实的,是枕边叠放的新衣裳。母亲用旧棉花一层层絮出的棉袄棉裤,蓬松得像云;手织的毛衣,每一针都藏着体温;缝纫机“哒哒哒”踩出的外罩,布料普通,却熨帖合身。
如今,人们总说年味儿淡了。手指动动,便能购得天南海北的美味和美衣。我们坐享“年”的成果,却拱手让出了“忙年”热气腾腾的参与感。年味儿,并非凭空而来,它藏在炸糕时溅在手背的油点里、藏在手写春联时凝神的眉宇间、藏在笨手笨脚却无比认真包出的第一个破皮饺子里、藏在一家人齐动手大扫除后,看着窗明几净时相视一笑的默契里。
我们怀念的老包头年味儿,是父母用双手从匮乏中创造丰盛,是我们在雪地里创造欢腾。如今,角色转换,我们成了父母。与其喟叹年味儿不再,不如亲手去“创造”年味儿。到厨房,和孩子捏一团面,看它在蒸汽里开花;到书桌前,裁一方红纸,写下对春天的邀请;甚至可以只是一起守岁,讲一讲过去的时光,滋养新一代人关于团圆、期盼与爱的记忆,让年过得有滋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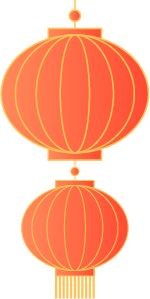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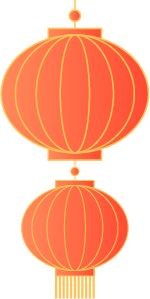
作者/刘清成
从小生长在包头厂矿里的人都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厂矿就是个小社会,有学校、托儿所、卫生院、俱乐部、粮站、副食店、百货商店等,足不出厂矿就能解决一切生活文化需求,所以厂矿里的年味儿也特别浓厚、特别暖心、特别难忘。
厂矿里的家属区非常集中,一排一排平房,家连家、院连院,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帮助,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大家都来帮忙。有时候端着饭碗就去邻居家唠嗑,小孩坐在邻居家炕桌上吃饭也是司空见惯。平时谁家包饺子、做好吃的总要给邻居端去一碗,谁家娶媳妇聘姑娘,厨灶就设在院里,宴席占用好几家,帮忙的人来来往往,整个巷子红红火火、热闹好几天。
如果赶上过年,那就更热闹了。先说年前吧,厂里把猪肉、羊肉、牛肉、带鱼按照职工人数分下去,把每户的凉房大瓮垛得满满的。
民谣唱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到了二十四,扫房子的时候,家里孩子少或者女孩多的家庭就明显吃力,这时不用愁,邻居家的老人早就嘱咐自己的小子:“明天你大娘家刷家,你们几个都去帮忙。”第二天这几个小子早早就来了,把兑好的大白(刷家用的一种白粉子)舀在瓷盆里,蹬上高凳子一刷接着一刷,横平竖直,一直忙到中午,看着各个脸上的白泥,像极了戏曲里的“小丑”,大家都哈哈大笑,晚上在粉刷一新的墙壁贴上散发着油香的年画,整个房间亮堂堂的,年味儿一下子就有了。
那时候炸糕,需要把黄米先用碓子捣碎,用箩子箩好,这是力气活儿,一排房子的邻居你帮我,我帮你,碓子和箩子在邻里之间传来传去。有的河北人、河南人不会烫糕面、炸糕、炸麻花,山西邻居就来帮忙,沏上一壶热茶,邻里之间说说笑笑,不一会香气四溢的油炸糕、麻花就出锅了。蒸馒头也是,邻里之间经常串着换肥面和曲红(用于给馒头点红点),有的还顺手给小孩脑门上点一个红点,特别喜庆。
厂矿里过年写对联可是一项苦差事,因为会书法的人少,几千副对联都要经过他们写出来,还要自备毛笔墨汁,但是只要邻里拿过来裁好的红纸,就一定要信守承诺,赶在大年二十九写好,哪怕一连几个晚上不睡觉,也在所不辞。你看吧,办公室、会议室、走廊里全是红彤彤的对联。等到大年三十中午贴对联的时候,因为平房门窗多,一贴十几副,邻里之间互相帮着贴,你贴个“抬头见喜”,我贴个“春风得意”,不一会儿整个街坊就喜气洋洋。
晚上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吃完饺子以后,有电视的人家挤满了人,大家围坐一起看春晚,其乐融融,屋里炉火通红,一团祥和的气氛弥漫开来。
初一早上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相互贺春。厂领导要带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人拜年,为他们送去饺子、水果、茶叶和最美好的祝福。晚上厂里俱乐部还要放焰火,大人小孩争相观看,烟花映着一张张笑脸,孩子们一阵阵欢呼,一年的烦恼随着这绚丽的焰火烟消云散。焰火之后就是工会组织的猜谜活动和放电影,电影从初一放到初五,让电影迷过足了瘾。那个时候厂俱乐部楼顶上都有大喇叭,过年期间有什么文艺活动大喇叭随时播报。
厂矿里最热闹的是正月十五。一大早厂里红红绿绿的高跷队和秧歌队就汇聚在俱乐部门前,伴随着锣鼓开始巡街表演,如果遇上临近厂矿和乡村的高跷队,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赢得一阵一阵喝彩声。晚上华灯初放,明月高悬,主要街道上,职工自己制作的各式各样、古香古色的灯展将年味儿推向高潮。
十五晚上的餐桌也是最丰盛的,街坊邻里围坐一起,互相谈论一年的逸闻趣事、酸甜苦辣,畅想新的一年厂里要为职工办的好事实事,最后大家共同举杯祝愿新的一年邻里和睦、阖家安康。
岁月流逝,时空变换,旧邻里早已各奔东西,容颜已改,但老厂矿浓浓的年味儿至今仍在心里萦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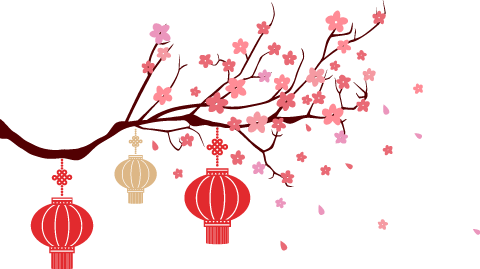
(责任编辑:吴存德;一审:张飞;二审:刘磊;三审:王睿)










